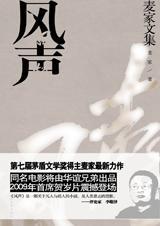风声-第2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部门统一代管,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具有的保密时限到了,方可归还本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每年都有一个解密日,每到这一天,她都要替母亲去单位看看,有没有她母亲的解密件。这天上午她照例去了,并且帮母亲领回来了一点东西,给老人送来时我还没有走,有幸一睹。
东西由一块蓝色丝绒布包着,看上去有点分量。因为已经解密,老人家当着我的面打开来看,是一只像框和几封书信什么的。像框上的人男性,六十多岁,戴一副金边眼镜,看上去像个有身份的人。
老人家一看像框,自语道:“看来他已经走了。”
女儿对她点点头。
老人说:“他比我还小十一岁呢。”
女儿说:“他是生病走的。”
老人摇摇头:“反正是走了,这下好了,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说着颤巍巍地起了身,要上楼去。
女儿似乎料到她上楼后不会再下来,关心地问我采访完了没有。我说没完,还有几个小问题。老人家听见了,回转身,对我摆摆手:“已经完了,我说得已经够多的啦,我都后悔跟你说了这么多。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故事结束了,你的采访也该结束了,不要再来打扰我了。走吧,我女儿会安排你回大陆的。”
她刻意地不跟我道再见,只对我说一路走好。我想,这种不必要的严谨应该算是她的职业病吧。
2
我的职业注定我有些游手好闲,喜欢游山玩水。我在浙江沿海长大,生于六十年代,小时候,只要夜空中出现什么异常的灯火,我们都会把它想象成是台湾飞机在空降特务。所以中国那么多省市,台湾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外省,比北京、上海都还先知道。那时我总把台湾想得很近,感觉就在山岭的那一边,长大了一定可以去看看。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其实是离世界很近,离台湾很远,你可以轻松去美国、阿根廷、冰岛、澳大利亚……却不一定去得了台湾,虽然它是我国的一个省。这么难来的地方来了当然要好好游玩一下,我订了一个五日游计划,台北、高雄、新竹、桃园、阿里山、绿岛……然而,每到一个地方,再美的景色都驱散不了老太太的音容,才玩两天下来,我笔记本上已经记有五大问题和一些小问题。五大问题分别是:
一、老鳖是怎么将情报成功送交组织的?当时他已被敌人全天候监视,而且整个事情发端就因为那天晚上他传情报给老汉时被敌人截获,那么此次传递又凭何保证不给敌人截获呢?
二、老人家几次说到,她发现李宁玉在用她的笔迹传情报后非常恨她,后来决定不告她并帮她把三只药壳子放回原地,是因为她怕李宁玉反咬,可最后李宁玉死了,其实已经不可能反咬她,她又为何还要帮她?
三、事后肥原把软禁在裘庄的人,包括张司令和部分工作人员都带走了,去了哪里?那些人后来均下落不明,是怎么回事?是生是死?
四、肥原到底是被什么人杀的?
五、老人家对潘老的情绪为什么那么大?是不是以前就有什么过节?
这些问题像毒瘾一样纠缠着我,让我无心观光,一心想去见老人家。几经联系均遭拒绝。到了第四天,绝望之余,我索性搭乘出租车私自闯去,可谓毒瘾发作,无法无天。老人家正在花园里纳凉午休,看到我不期而至,惊诧之余,她像个普通老人一样,摇头叹息,喃喃自语地费劲。我没有道歉,因为我知道道歉只会唤醒她犀利的心智,对我不利。我略施小技,先声夺人:
“我不请自来,是因为我觉得您有些说法经不起推敲。”
“怎么可能?”这一招果然灵,老人家出招就是辩解,“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要的就是她的辩解——良好的开端预示我将不虚此行。
果然,老人家对我提的问题很重视,几乎大大小小都作了认真回答。只有最后一个大问题,就是她对潘老的情绪问题,她显得颇不耐烦,只丢给我一句话:“你别提他,提起他我就心烦!”
我感觉两人以前一定有过什么过节,但有什么事会让一个古稀老人依然如此不能释怀?我人到中年,已经越来越相信一个哲学家的话:时间会消逝世间所有人为的颜色,包括最深刻、最经典的爱恨情仇。也许借用哲学家的话可以扰乱她的阵脚,引发她一吐为快。然而我实在不忍心,我已经很满足了,有些东西捅破了也许还没有封存的好。
3
当然,有些东西是必须捅破的,比如问题一和二。
对问题一,老人其实不是当事者,好在后来她曾去牢房见过老鳖,多少了解一点情况。老人说,那天晚上肥原没有抓到老K等人,断定这些人中必有老鬼的同党,于是,回来即把老鳖抓捕归案,连夜审问,想从他嘴里知道到底谁是老鬼的同伙。但老鳖宁死不说,所以肥原应该是至死也不知道底细。后来肥原走了,老鳖一直被关押在牢房里,有一天她偷偷去看他,那时老鳖的有生之日已经不多。正是那次见面,她从老鳖那里了解了不少情况,包括他是如何把情报传出去的。
“老鳖告诉我,遇到突然丢给他的特急情报,他必须马上看,然后根据情报的紧急程度作出不同的处理,最紧急的处理方式是去邮局直接打电话。”老人解释道,“这当然有点冒险,可能让敌人获知他组织上的电话。但有时候该冒的险还是要冒,没办法的,干我们这个工作本身就是冒险,脑袋别在裤带上的。老鳖说他后来就是打电话通知组织上的,因为太急了,其他方法都不行,只有铤而走险。他这一走险反而好了,因为敌人不可能贴身跟着他,总是有一定距离的,即使看到他在打电话,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情报就这样传出去了,李宁玉算是没有白死。”
我紧接着抛出问题二。老人一听,神情一下变了,变得激动,伤感,感慨万千,后来说着说着竟然忍不住呜咽起来,一个古稀老人的呜咽啊……擦了一把热毛巾,喝一口温水后,老人才平静下来,对我再度回忆起那天晚上发生在厕所里的事情。老人说,那天晚上李宁玉是跪在地上把三只药壳子交给她的,而且一跪不起。
“她要我对她发誓,一定要帮她把东西传给老鳖,否则就是不肯起身啊。”老人家连连摇着头,仿佛又亲历现场,看到李宁玉跪在她面前,“我拉她起来一次,她又跪下一次,反复了好多次啊。我本来确实不想对她发誓的,凭什么嘛,你求我办事还要我发誓,哪有这道理的?可她就是那么绝,跪了又跪,最后膝盖都跪破了,鲜血直流,血淋淋的。我实在看不下去,只好答应她,对她发了誓。说老实话,我后来犹豫过帮不帮她,毕竟这也是有风险的,但每当犹豫时我总是想起她对我长跪不起的样子,脸上泪流满面,裤脚上血淋淋的,可怜哪!可叹哪!人心是肉长的,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是在一念之间促成的。”
老人的话,我没有理由不信服。
对问题三,老人告诉我,事后肥原确实把她和那些人都带走了,因为他到最后也不知谁是老鬼的同伙,只好把人都带走,弄去上海审问。但到上海后她和那些人分开了,她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后来只有王田香和她被送回部队,另外那些人的下落谁都不知道。“估计都不会有好下场,即使不是死,也是生不如死。”老人家如是说。
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人杀了肥原?对此,老人家一点不谦虚,明确告诉我是她,并把杀人的时间、地点、人员、方式,有关细节,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总的说,她是花了四根金条从黑社会雇了两个职业杀手把肥原干掉的,按照要求杀手把肥原碎成三段,抛尸街头。我问她为什么要花重金去杀他,老人家久久盯着我,末了,闪烁其辞地告诫我:“有些人一辈子都在试图努力忘掉一些事情,你去追问它是不道德的!”
此刻,说真的,我已经从王田香的后人那里了解到个中隐情,但我决定不公开。我要替老人保守秘密,无怨无悔。我可以想象,老人家所以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一定是为了想让她这个秘密永远不受侵扰。现在她说得已经够多的了,就让我们为她沉默一次吧。不要因此有什么遗憾,事实上这个世界沉默的事远远比公开的多。
·18·
外部 静风
1
静风一词是气象专业术语,通俗地说,就是无风的意思。
其实风总是有的,有空气流动就有风,只是当这种流动小到一定程度(每秒零点二米),我们感觉不到而已。人的知觉很有限,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见,听不到,感受不到,但它们就潜伏在我们身边,甚至比那些有目共睹的东西还要影响我们的身心。
我把本部称为外部,不是玩花哨,而是想表明一个意思:有关李宁玉的故事已经结束,本部说的都跟那故事无关。跟什么有关?不好说的。我觉得,除了跟那故事无关外,似乎跟什么都有关,杂七杂八的,像一出生活,什么事都有,就是没有连贯的故事。有人说故事是小说的阳面,那么这就是阴面了。出于迷信,本部的每一个字我都选择在夜晚和阴雨天写成,我想选择同样的时间阅读也许会有些意外的收获。据说有一本书,一六九一年出版的《哈扎尔辞典》,读者在子夜后阅读它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保证我的书不论在何时阅读都不会招来任何祸水。
2
东风引发了西风,一场横跨海峡两岸的舌战势在必然。
从台北回来后,我一直在回避潘教授,他不知从哪儿探听到我去台湾拜访了顾老人家,短时间内先后给我来了一封邮件、两个电话和多条短信,问我行踪,表示很想见我。我以在乡下赶写稿子(事实也是如此,我在写下部《西风》)无暇见他搪塞。我似乎是受了顾老的影响,对他有情绪。其实不是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和实际,可以说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心理。有些东西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见面绕不开要说起顾老讲的故事,他听了一定会组织人力予以反击。潘老是首当其冲的中锋大将,靳老(即老虎)和老K的长子林金明可以当个左右边锋,王田香女儿王敏和哨兵甲可以打个后卫,还有部分党史研究人员做个声援的啦啦队也是够资格的。一年前,正是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帮助我完成了上部《东风》,现在有人要对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进行毁灭性的剿杀,他们怎么可能袖手不管?一定会集体反击的!
如果反击无力倒也罢,反之则将严重影响我写《西风》的热情。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开潘教授的追踪,避而不见。我早想好了,先写出来再说,完了给他们看,听他们说。他们怎么说都可以,我将努力做一个聪明的传声筒,争取挑起双方打一场时髦的口水仗,让他们把想说和不想说的真话、假话都一股脑儿端出来,接受世人的评判。
3
乡下是让人慢下来的地方。在这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徒,非亲非故,无是无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和精神都消耗在慢慢的回忆和等待中。等待是对速度的向往。换言之,主观和客观都为我的写作加快了速度,所以我有理由在给潘教授的邮件中自豪地写道:我相信我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稿子,希望你阅后尽快给我回音……我是说尽快:一个带着速度的词,所有的撇捺都是翅翼,驾驭着它从我们眼前一掠而过,洒下一路呼啸。
4
潘教授的回音姗姗来迟,而且严格地说,不是回应,而是报丧:潘老寿终,希望我去参加追悼会。我突然有点害怕,担心是我的稿子——顾老讲的故事——把他气死的。话说回来,如果确凿如此,我更应该去追悼。我没有选择,惴惴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诉我他父亲正是在看我稿子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贯的口吻,文质彬彬又带着思辨的色彩对我这样说:
“毋庸置疑,你的书稿是直接导致我父亲去世的诱因,但不见得一定是被气死的,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七天,其间多次想开口说话,终是一语未破,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的。这也符合他的身份,带着秘密离开我们。”
我感到无地自容,像害死了一个婴儿,不知该如何谢罪。
潘教授非但不责怪我,反而主动宽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书面语言:“对一个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临的课题,甚至一个突发的喷嚏都可能让他走。你起的作用无非就是一个喷嚏罢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父亲唯一的子女,父亲走了,我可以代表父亲向你承诺,我们潘家人决不会追究你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