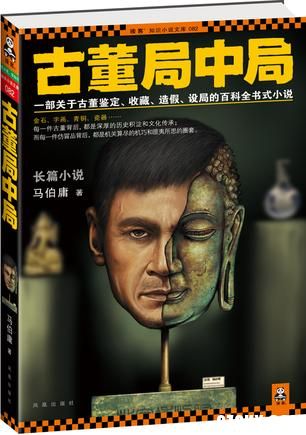古董杂货店 →蒋胜男、匪我思存、飞樱-第27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情,亦真亦假,有些亲眼见的、亲耳听的,也不见得就是真的,有些见不到证据的,倒也未必是假的。就像这壶吧,是不是只好壶,还得你自己有个定断。”
苏星呆呆地愣了半天,回过神时,女子已经不在眼前。
她忙忙地追到门口,却只见黯淡的斜阳,静静地照着空荡荡的小街。
苏星既是作家,也有些作家的通病,譬如白天睡觉,夜来伏案。
所以,侯洙也只得每天入夜来找她。
那五百块钱,当了一个礼拜的借口,一个礼拜之后,他便也不再找什么借口,依旧日日来访。也不知他这一世以什么谋生,接连一个月,天黑下来便准时到,倒像上班一样。
他来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做,有时苏星写作,连话也不跟他说,他也不打扰,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旁边,也许手里拿一本书,但苏星从眼角打量,大多时候,他并不在看。
他总在看她,深深地深深地看,目不转睛。眼神里有很多内容,似乎有探究,似乎有迷惑,更多的还是依恋。
这样专注的目光,让她忍不住心酸,也忍不住犹豫。
可每当这种时候,恨意便像潮水一般涌起,心又硬起来。
这天,苏星告诉他:“我正在写一部小说。”
她正坐在窗边,这时已经是暮春,窗子大开着。将满的月在她脑后,莹白的一轮,映着她的脸庞,仿佛也泛着淡银色的光泽,虽然美,却有着一丝诡异的味道。
“以前我写的都是空洞的故事,可是这一个不同。”她微微侧过脸来,“你想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吗?”
侯洙点了一下头。
“我要写一个舞妓,她的名字……”她看了看手里的连理壶,“她的名字叫绛彤。”
思绪有些乱,她停下来。
侯洙忽然笑笑说:“那么她若有一个情人,就该叫子安了?”
苏星望着他,眼里流露出淡淡的哀伤,脸上却笑得明媚,像个被识破小诡计的孩子,“对了,她的情人就叫子安——我的灵感,正是从这壶上来的呢。”
侯洙没有说话,她便也跟着沉默了一会儿。
“绛彤那时,是乾隆年间的名妓,那既是一个太平盛事,人物风流,绛彤也很有些际遇,慢慢地便眼高于顶,倒把自己看得跟个侯门千金一般。”
她不由得一阵苦笑,那时也不过十几岁的年纪,叫那些个公子哥儿们一捧,便不知天高地厚起来。
只可惜,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侯洙忽然说道:“她一定是位才貌双全的绝世佳人。”
她想了一会儿,点点头说:“大概是吧。她有七步成诗的才气,也有一舞倾城的姿容。她那时,喜欢穿大红的绸衣,因为爱这喜色,欢场已经诸多辛酸,为何不叫自己快活些?她便日日穿着大红的舞衣。也不知引得多少章台走马的贵介,掷下千金,只求一睹芳容。”
那时,日日欢歌,也觉得平常。
直到遇见他。
“子安那时候是个公子,他的父亲是当朝大学士,姓富察……”
苏星叹口气,富察公子。
京中公卿第一族。
也不是没有忌惮的,连鸨儿都婉转地劝过,但一见他温柔的神情,便什么也不顾了。
“那怎么呢?”她对着鸨儿半蛮横半撒娇,“将他拒之门外?”
谁敢?谁敢将富察公子拒之门外。
有富察公子在,别的客也不必接了。于是,便有双宿双飞的日子,花前对斟,月下吟章,仿佛称心如意。
她从来未曾提过要他娶她。
不愿提,不愿叫他觉得她别有所求,也不必提,其实那一个名分,对她来说没有多大用处。她富有积蓄,待到年迈,宁可效法鸨儿,在八大胡同寻个安身处,也不想去那公府中低眉顺目。
但他不肯。
他总是很固执,再三坚持。那时年少,也就答应了——
“绛彤那时,满心地信任子安,他说爱她一世,她便信了,他说花轿来迎,她便也信了。”
侯洙眼里闪动异样的光芒,“后来呢?”
“那一晚,本是子安与她相约,来迎娶的日子。”
“结果,他践约了没有?”
“结果……”她说不下去。
恨意一点点地积起来,像针一样扎在胸口。
侯洙一直深深地深深地注视着她,那目光也像针一样扎在胸口。
“你走吧。”她忽然说。
说完自己也愣了,好不容易下决心到了这一步,为什么要让他走?
可是想了一想,还是说:“你走吧。”
侯洙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手扶着门说:“我明天再来,你把这故事讲完吧?”
苏星怔愣了许久,终于无可奈何地笑笑:“好。”
侯洙的脚步沿着楼梯慢慢地走远,苏星的心里便怅然若失起来。
丝帕
一个人坐在窗边,已经有一点暑气,入夜不散,燠热便仿佛一直闷到胸口,呼吸不畅。
目光忍不住往窗外望,看那一条树影摇曳的小径,渐渐行远的人影。
他的脚步,似乎很是犹豫,几度停下来,她以为他会回头了,忙忙地转开视线,但他却不曾真的回头来看。
那时却不同。
每一回他走,都一再地回头,她便在楼上挥一方雪白的丝帕,故意要他看见,故意要他回头。
那丝帕的角上,绣了一双并蒂莲。
那一回他走,她故意地,失落了那丝帕,像一朵云般,飘落在他脚边。他便拣起来,仔仔细细地收起,把那一双并蒂莲,收在了怀里。
连理并蒂。
苏星的手在连理壶壁上慢慢地摩挲。
那壶,本是他亲手递到她手上。
因为她提起曼生壶的别致,他便辗转相托,特为请陈曼生做了这一只。曼生十八式不载这一只,人世间惟有这寥寥的几个人知道根底。
所以,那一晚,她便穿着大红的嫁衣,在红烛腻人的光影里,捧着这一只壶,静静地等,静静地等。
不虞有他。
想起他临去时,执起她的手,似乎有许多的话,却只说了两个字:“放心。”
她那忐忑的心,便真的安定了。
侯洙再来时,发觉门开着。
苏星坐在窗口,手里捧着连理壶,那模样,仿佛自他走后还不曾动过。
侯洙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他总是坐在这个位置,刚好看见她的侧面,日日来,已经成了习惯。
逢十六,仍是月圆。清辉洒在窗台上,也洒在她脸上。侯洙看了她一会,又慢慢地转下去看她手里的壶,那珠圆玉润的壶壁,便在月光泛着莹莹的光,看来竟有几分妖异。
苏星忽然回过头,很奇怪地看看他说:“你来了。我还以为今天你不会来了。”
他微微一笑,“我说过要来,就一定会来的。”顿了顿,又说:“如果你真的以为我不会来,为什么要把门开着?”
苏星淡淡地说:“这是两回事。我开着门当然为了等你,可是我等你,你就一定会来吗?”
侯洙觉得她的话很奇怪,怔了一会,没有回答。却问:“那么,绛彤到底等到了子安没有呢?”
苏星转过脸来,见侯洙目光炯炯地望着自己,忽然一阵说不出的烦恼。她摇摇头,焦躁地说:“我想不好!我也不知道,绛彤等到了子安没有?”
侯洙笑笑,说:“那你慢慢地想,我不会着急的,无论多少时间,我都可以等着你想出答案来。”
这不是她设想会听到的回答,苏星便有些不知该如何是好。望着月亮发了会儿呆,她低低地问:“你相信有些事,是前世注定的吗?”
侯洙回答:“如果一个人不记得前世,那就算被前世注定,也没有什么意义。除非一个人能记得前世,那今生也许能被前世注定。可是一个人,真的能记得前世吗?”
苏星默然,半晌才道:“听说一个人的恨意若是能够上达九天,就能够三生三世都记得这段仇恨。”
侯洙静静地看着她:“真的会这样吗?”
苏星摇摇头,又点点头,“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
侯洙忽然笑了笑,“听你这么一说,我倒也有点相信起来。”苏星不说话,他便又说:“你知道么,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很面熟,可是我并没有见过你。现在听你说前世,我想,我也许是认识前世的你吧。”
“哦?”苏星勉强笑了笑,“你怎么会这么觉得的?”
侯洙说:“我不但这么觉得,而且我想,我一定很喜欢前世的你。你说恨一个人可以记得三生三世,那喜欢一个人也一样吧,不管你怎么转世,我都会喜欢你。”
苏星不由地失神起来,可是心里就像有一根冰凌,又冷又尖锐,狠狠地刺下来,便又惊醒过来。
“你不是想知道绛彤有没有等到子安?”她说,“现在我想到了。”
“等到了没有呢?”
苏星低头望着手里的连理壶,钮子旁边的花开并蒂,红艳艳的,却像针一样刺着眼睛。
她慢慢地说:“她等来了,来的却不是子安。”
是两个富察公府的家人。
拿着子安的绝情信,那方绣着并蒂莲的绢帕,还有……一杯鸩酒。
话却只有一句:“花轿,你也配!”
你也配。
只这三个字,如同三把刀,将她一段段地切,一寸寸地割。抛进油里,又抛进冰水里,从来没有过这样热,从来没有过这样冷。
人僵了,心也木了,连那酒如何滑过喉咙都没有感觉。
只是不甘心。
什么花开并蒂,什么连理同根,原来全是镜花水月。
但,她并不曾求过他呀。
死死地捞住那最后的一丝自尊,如同捞住沦入泥沼的落红,什么绝世有佳人,自欺欺人罢?命里注定要被人踩的。只是不甘心,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他,来踩上这最后的一脚?那么狠,那么不留余地——
“后来呢?”那男人问。
她冷笑,“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后来?”
侯洙不语,良久,忽然长叹:“原来结局是这样,我倒是不曾想到。”
她问:“那你以为结局该是什么样?”
侯洙想了一会,说:“那子安原来想将生米煮成熟饭,逼得家里不得不认下儿媳。他在外面赁屋,备下喜宴,那一天,他本来该去迎娶绛彤。却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都不曾瞒过府里,才出门就被捉回。等他终于脱身回去泉香楼,绛彤却已经死了。原来家人告诉她,子安已经另娶,绛彤便仰药自尽——”
嫁衣
苏星冷冷地望定他:“你想说,这一切子安都不知情?”
侯洙默然片刻,苦笑了笑,说:“这结局是不好,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绛彤是个刚强的女子,便是情郎真的将她抛弃,她也会活个好样儿的,绝不会自尽。”
苏星心里蓦地一酸,想不到转过来世,他还是如此了解她。那一世,他便是这样的,叫她以为他是个知己。
呆呆地出神,忽听侯洙问:“我还是不明白。绛彤那样聪明,为什么会轻信那两人一定是子安派去的?”
“有他亲笔的绝情信。”
侯洙叹息,“可以是别人代笔。”
“还有那方绢帕。”
“可以是硬抢来的。”
苏星忽然不语,咬了咬嘴唇,一点殷红慢慢地渗出,刺目如同并蒂的花瓣。
侯洙若有所思地看着她:“这故事还没有最后结局吧?”
“人都已经死了,还要怎样才算结局?”
侯洙一笑,“可是我却总觉得,还没有到最后的结局。”
苏星沉默良久,终于慢慢地点点头,说:“是,还没有最后的结局。”
“那么后来呢?”
后来?……后来清醒过来,已是一只鬼,一只不甘心的鬼。
纵然已是一把破碎的玻璃,拾掇不起,却总还不肯死心,便在世上游荡。一只孤魂野鬼,被那一腔的恨燃烧着,被那一丝不甘心冰冻着,满怀心事地游逛。
好生辛苦,这世上却鬼的宝物太多,一出门,寸步难行。
费了好多气力,终于到了公府。
却只见双双对对的红灯笼,喜字灯笼,红得如同并蒂的花瓣。
她怔愣间,便见一乘大轿缓缓地来。
他在里面。
到底是鬼了,不消看,也感觉得到,便不由自主地跟。
二门轿停,看他下轿,携一个女子的手,下轿。
当朝的公主。
那是他的妻,配得上他的妻。
怪不得。
怪不得,不能再容一个青楼女子,坏了驸马的名声。
看自己身上,尤是那一身喜服,一枝梅花攀上,一双喜鹊婉转,有道是“喜上眉梢”,玲珑精致,一并艳艳地嘲笑曾经的不甘心。
还有什么不甘心?没有了。
终于,彻底地,死心。
只是这段仇恨,却不肯忘却。
三生三世,定要找到他!定要他偿了这条命!
她出神地想,不由笑得狰狞。
忽听侯洙说:“你穿这红色旗袍,倒真有几分像新娘子。”
她一怔,浅笑:“原来你留意到了,我特地做的。”
“我一进来就留意到了。”侯洙上上下下地打量半晌,又说:“要是件嫁衣,还应该再精致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