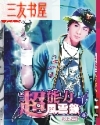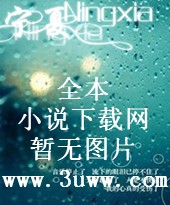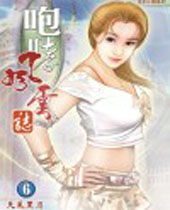外交风云亲历记-第47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凝重,他一直在思考着什么。我当时感到周总理对着一个下级同志,也只能这么说。
“维特克女士当场作了笔记的,而且有关江青同志个人历史部分,我们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她要写文章,材料是足够的。”我见周总理在默默深思,说完后就悄悄地退了出来。
又是一个夜晚,在10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第九部分第117节:周总理与《谈话记录》(2)
当年11月间,维特克女士从美国寄来数幅已经放大的江青彩色生活照片。维特克说她已经写好了一篇报道江青的文章,准备登载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封面就用江青的彩色照片。由江青选择其中的一张,并盼赶快把所有记录稿寄去,以便她着手写书。江青收到照片之后高兴极了,把维特克寄来的以及原有的不少照片,摆在钓鱼台她那张大大的长方形的办公桌上,反复仔细地自我欣赏,挑来挑去下不了决心。于是打电话到外交部,把我们当时在场的几个人,用一辆面包车拉到钓鱼台10号楼去。
江青十分专注地看自己的照片,直到我们一群人走进办公室来,江青才抬起头说:
“好呀,你们快来看看这些照片,这是维特克女士寄来的。我觉得坐在栏杆上的半身像不错,当然还是不如我自己拍的那些色彩好。”我们分成三三两两在看那些照片,但谁的兴致都不高。江青拿着那张半身的照片,先问徐和小沈:
“你们看看,这张不错吧,有点侧着身子,光线还可以,就是色彩淡了些。”小沈和徐也就点头微笑。江青又叫:
“小张,你学过点美学吧?你看是否把照片裁短些会更好看?”江青用厚纸盖着下端,上下比试,我走过去看了看说:“裁短就没有手了。”江青又上下比试好一会儿,吩咐小沈给维特克女士写回信。江青兴奋好一阵子,但以后谁也没有看到《时代》杂志有江青的照片用来作封面。
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整理稿送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
某日下午,周总理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维特克女士与江青的谈话记录如何处理的问题,把所有参加过接待维特克女士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周总理征求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同志表示,这份记录无需送给维特克女士,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的。而维特克女士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后边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要逐一核实,得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而且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周总理当时一言未发。对任何一件事的决定,他都要作仔细思考,并广泛听取意见,尽可能做得完善些。会议结束前他说:“对这件事情,你们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很好。但今天还是决定不了,还需要商量和请示。”他对我和徐二人说:“你们继续去作记录,根据江青同志的要求整理和修改。”
又一天晚上,我和徐来到10号楼,继续修改记录稿。12点已过,已经接近完成了。我们到大食堂吃过夜宵后回到江青办公室,她正在打电话,声音还挺大的:
“我的那些个记录,一本一本都给你送去了,怎么不快替我看呀?”
“…………”
江青:“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我答应过人家,就得给。”她想做什么像是谁也阻止不了似的。
“…………”
江青又立时换了腔调:“总理呀,你就替我审查吧,不给维特克,那可不行,唉呀,我看到你桌上堆的那些个文件,我真替你累得慌。不过那些个记录,你还是得替我审查。”
“…………”
“一定要给,我不能失信于人,就得这么办。”江青又变了调,横不讲理。
“…………”
“哼,他们呀,就只划了个圈。我说总理呀,不送给维特克我可不答应。”
江青把电话放下,一脸怒色,眼睛都不往这边瞧,我们都默默地坐着。
江青吃过夜宵,好一阵才平静下来,拿起一本记录在翻看。这本记录中是谈她和毛主席生活的。其中有几段涉及到很多人,还有贺子珍及孩子。
整理记录稿时我将这几段的对话删掉了,徐正读着,江青突然问道:“哎,怎么这部分少了些内容?小张,是你先看过吗?”我点点头。
江青声色俱厉:“怎么?是你改了?谁让你改的?”
“我没有改,我删去一些。”我直直地望着江青的眼睛,倒使江青一怔,她接着追问:“你胆子不小呀,哼哼,你居然敢删我的记录?说说什么理由?”
“那些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认为不提为好,何况你用那种语气来谈另一个同志,不大适宜。”其实我是出于某种责任感,已经许久没有人再提这些事了,又何必再引起新的麻烦呢。所以才删一点过分的小节。我本已想到,会引起江青的怒火,但在广州时已经历过了,怕也无用。她对我已恨在心头。
江青发火了:“有什么不适宜?”
“和你现在所处的地位和身份都不适宜。”
江青在室内踱着步,右手拿着支铅笔敲打自己的左手,喃喃自语:“唔唔,我现在的地位和身份……自己这么说是有点不大好。”然后冲着我说:“这些内容是不能没有的,我和主席结婚是光明正大的。我不能是第三者。”她来回走动,恶狠地突然对我说:
“小张,这段话改为你的语气由你说,我想是可以的。”我真没想到,江青会想出这样的绝招,一时有点呆住了。
第九部分第118节:周总理与《谈话记录》(3)
那座大钟滴答滴答地声音,显得特别响,一下一下像击打着我的心。“我不同意,这又不是我说的话,怎么可以变成我说的呢?”我平静而坚定地说。
江青:“反正要这样的内容,谁说都一样。这对你也无害嘛。”
“我在延安的时候,还是个学生,也不可能知道这么些事呀。还是删掉算了。”
江青顿时狂怒,拍桌子大骂起来:
“好呀,张颖,你就是不听我的,告诉你,这可不是小事。这是站不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问题。你不和我站到一边,就是站到相反的一边,你想想看,会有什么结果……”我看到江青发火,也不止一次了,虽然都是横不讲理,但不像这次狂怒,而且扯到革命反革命的高度。我想这股火也不是单冲我来。我瞪着眼,无话可说。室内空气十分紧张。
“老张同志,你是首长的学生,这些事情嘛是可以说的。难道在延安的时候,你没有听说过吗?何必让首长发那么大的脾气呢?”那位局长想缓和一下僵持的局面,慢声细气这么说。我一闪念,可有了救星,立刻接着说:
“对了,局长同志,你来说这段话比我合适得多,就写在你的名下吧。我是学生,不好谈论这些,而你是江青同志的战友,分量就大不一样了。”张局长一听发了呆。
第二天,我觉得筋疲力尽,请假在家休息。傍晚时分,忽然听到敲门声,一开门,好熟的面孔,一时竟认不出是谁了。
“你不认识我?”客人说。
“是你呀,阿晨。”我走向前紧紧抱着她。阿晨的泪水簌簌下流,直至痛哭。
阿晨是郑君里的妻子,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虽然分住在北京和上海,还是常常见面的。但“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些朋友谁都没有好日子过。尤其是文艺界知名人士,全都成了牛鬼蛇神,彼此也不能通什么消息,只能从各种传言或那时特有的小报上,知道一点彼此的消息。我看着阿晨,这几年她变得如此衰老,消瘦,满脸皱纹,头发花白,不禁悲从中来:
“上海的同志们都怎么样?君里呢?”
阿晨好容易镇定下来:“在劫难逃啊,一个也饶不过。唉,君里君里……他……”又悲痛起来。我倒来一杯水,劝她安静休息一下。
“死了的,也许你已听说了。活着的都在受罪。君里真冤枉,五年前就被抓走了。开始时被隔离在厂子里。有一天深夜,也弄不清是谁,既不像公安又不像红卫兵,闯进了我们家,到处乱翻,什么都折腾了,最后把所有照片,所有写过字的纸条统统拿走,把能砸的都通通砸碎,留下一间小屋子让我睡,其余的房子通通上了封条。1969年初小儿子去探望过,才知道已经被关进监狱。
“关在哪里?”
“哪里去问,哪里去找呵。整整三年没有消息。前两个月,忽然叫我去探视,那就是监狱医院吧。唉!白单子把全身盖着,简直像死人了,只剩下一丝游气,他告诉我,是为了那张结婚照片……”
阿晨饮泣。
“那就是君里、阿丹我们四对,在杭州时一起照的相片。几十年了,谁还留着这些东西啊,而江青就为这些,要把君里他们都置于死地……我好不容易来到北京,看看朋友们,是不是可以想点办法,给君里治治病,不然太惨了……”我们两人互相拉着手,默默相对,各自流泪。
1972年的岁末,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于是第二天,我和小徐、小俞把所有的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
第十部分第119节: 旁听审判江青(1)
1973年秋末,我调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政务参赞。这里已经远离那令人窒息的北京城,但心里总装着祖国,时时关心着那里发生了什么。年底,北京在大张旗鼓地掀起一个新的运动高潮,那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虽然国内的消息大都被封锁,但时常还会传来各种信息。江青一伙想要彻底摧毁我们国家的基础,她真想当女皇了。
岁末年初之际,国内来了一个代表团,团长是老同志老朋友了,他把国内的情况告诉我们:这次批孔批大儒是公开地向周恩来总理发起全面攻势了。并且开了万人大会,炮轰大儒,国内又乱起来了。但江青的做法不得人心,对她的不满和闲言也挺多的,攻势也弱了下去。又说现在国内正闹着《红都女皇》,为这江青还挨了批评。美国有个女记者采访江青后写了这本书,现在全国都在追查谣言。
我被这位国内来的同志谈话中的许多事情都弄得糊里糊涂的。他问我《红都女皇》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据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华人写的,吹捧江青的。但这与维特克采访江青完全是两回事。维特克是个美国人,她采访江青以后要写的书,还没有写出来哩。他又告诉我,国内盛传毛主席批评了江青,这恐怕是确有其事,但现在国内也正在追查谣言,说那个美国人采访江青就是谣言。我说这不是谣言,因为江青会见维特克这件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登载过的,而且当时我也在座,这都是事实。
1974年秋末,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国内的气氛还真有点不一般。全国追查谣言的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而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据说《红都女皇》那本书从香港进入以后,引起一些不良影响,江青也被批评。但和维特克又怎么联系得上呢?
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特别去找了小徐,她知道得比较清楚。她说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