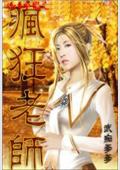疯狂医生-第2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叫韩寒;炒作这事,如果干得好,叫《英雄》;胡搞这事,如果干得好,叫木子美;偷窥这事,如果干得好,叫美国卫星;扔黑砖这事,如果干得好,叫本·拉登;烧钱这事,如果干得好,叫电子商务;玩游戏这事,如果干得好,叫加班;发不了工资这事,如果干得好,叫共同创业……”
老实说,这是迄今为止我最喜欢的一个文字接龙游戏,在我看来,如同那个在网上也曾风行一番的“等咱有了钱”男女生版的接龙游戏一样,这无不都代表了民间广大人民的聪明才智,虽然说老把聪明和才智放在游戏上面总有些不务正业的感觉,但偶尔的剑走偏锋也未尝不可——反正生活都像“大水和龙王”之间流产的官司这么枯燥和无聊,还是别太累了。
第四部分 情圣泡妞第43节 明星选拔
对于一个体育迷来说,所谓的幸运,就是在他刚刚回到家之后,顺手打开的电视机中,正在播放着他所深深喜爱的体育节目;所谓的惊喜,就是这个节目恰恰叫他梦寐以求地等待了数年;所谓的心花怒放,就是一听体育就头疼的太太回了娘家;所谓的合不拢嘴,就是多年不见的球友刚打来电话,告诉你他今天晚上跟你一边通宵看比赛,一边杯酒醉方休;所谓的‘HIGH’到极限,那就是医院的领导发来短信,告诉你说,明天单位休假一天!
当然,以我沉重的历史经验来看,本人遇到这种好事的几率大概为零。如果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也只能勉强达到0。01%。但不管怎么说,对于那些体育迷们来说,的确有一个豪华盛宴被享受了。在一个凌晨夜晚的1点半——大部分人平时睡得最香的时刻、欧洲足球最喜欢比赛的时段、春节时在饭店吃完团圆饭刚刚回家的钟点、希腊当地“星”光璀璨的瞬间,2004年奥运会,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体育盛会,已经在爱琴海边完成了。
在不久前的欧洲杯上,一个花了60亿欧元的奥运会东道国战胜了一个花了6亿欧元的欧洲杯东道国,一个65岁的德国人战胜了一个56岁的巴西人,一个不知是否真实存在过的瞎子写的神话战胜了所有道学家、哲学家、技战术家写的教材——一个靠11个人防守,像机器一样严密防守的球队战胜了所有进攻主义的大师。希腊已经把神话写进了欧洲每一个人的心里,现在,他们还要把神话告诉全世界的人民,所以,这个开幕式变得别开生面,而又失水准。我没有把握断定希腊人的开幕式本来是拟订好的,后来因为足球欧洲称王而改变,但我还是从中看到了一丝希腊人的自豪与骄傲。
巨者大喜,渺者小乐,好的感觉是一样的。除了希腊人,同样骄傲的还有姚明。相信很多人已经看过开幕式了,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再多费口舌在这里将繁琐的过程再复述一遍,只不过在与开幕式有关的新闻里,最吸引我的,却是姚明的升旗仪式。据新华社的记者报道说,当一名升旗手是姚明儿时的梦想。在雅典奥运会上,他的这个梦想换了一个方式即将变成现实。姚明说,他上小学的时候非常想当一名升旗手,但是,他苦等了小学5年也没有被老师选上。这件事让姚明一直有点遗憾,不过他解释说,小学的时候自己确实不那么显眼。
有NBA上风光无限的姚明在前面“垫背”,我要硬说自己的梦想也是升旗,就显得有些热脸往什么地方贴的意思了,但实话实说,我确实有一种希望,就是能够升一次旗当然,我指的是小学里,现在我只能业余时间和一帮老头儿们踢踢足球,为祖国拿冠军夺金牌是绝对不可能的了,若想用体育成绩来打动奥运会的那些老头儿们,叫我去代替姚明升旗也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在小的时候,我的这个梦想却是真实存在的。
令我迷惑的是,至今我也没能弄明白,学校里选拔那些升旗同学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如果按身高,我就算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红旗下面揪那根儿象征焦点的绳子,当个护旗手也应该没问题吧;倘若按学习成绩,小时候我还没有现在淘气,不管名次还是分数也都名列前茅,怎么着也能露个小脸儿的;要是按相貌的话,我长得虽然没有姚明帅气和精神,但那时候那个升旗的同学可比我丑多了,而且那时候也没听说过流行“注意力经济”的。
所以这不禁叫我感到深深的不解和疑惑。不光是我,办公室的乌鸦,一个经常叫嚣自己长得可以当周杰伦的同胞弟弟的家伙,也着实郁闷了一把:今天早上,医院传达了最终赴市里参加演讲比赛的人选,就连丑如NBA大鲨鱼的卫生局赵干事都有,可就是惟独没有他。其实谁都知道,乌鸦想参加比赛并不是想夺得名次,而是看中了那丰厚的假期和奖金。
得知这个消息后,乌鸦在背后恨恨地说:连长得像周杰伦的明星种子你们都不要,还选拔个P呀。
负责选拔人员的牛主任对此的解释是:周杰伦唱歌的可以,但演讲不行。
宁哭不笑
人在极度无聊的时候会很变态,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因为我就干过这事儿。记不得在哪年,我被空虚包围后,曾傻呼呼地设想过自己的生命终点,记忆告诉我,它应该是这样的:在即将离开这个实实在在的世界的前夕,我将躺在一张偌大而温暖的床上,用颤抖的手跟一大堆儿子孙子一一告别,含着浑浊的老泪,挣着的微眯的双眼,儿女们无一不是热泪盈眶,拼命地向我表达着他们的留恋之情,等到最后,我点开一个个记忆的文件夹,进入一个个信箱,将自己写的、来自别人的一个个文件浏览一遍,再逐个删除,打开回收站,清空。我在老伴儿的陪伴下静静的看着电脑删文件;文件删完了;我也该走了……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
由此可见,我还是比较害怕孤独。前几天闲暇在家,看《花样年华》和《2046》,最后发现一条规律:把简单的事情办复杂了,这就是王家卫的特点。之后告诉猪头老婆阿童木,被其延续总结道:把一般的感情弄得理想化了,这是我的特点。阿童木说这个不是没有原因,我因为老喜欢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大惊小怪的诈唬,一再令她忍无可忍。比如说,在一个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里,特别是赶上重阳和中秋这样的节日,我总会象一个玩玻璃球的小屁孩儿一样思念起自己的双亲,然后再把这种感觉放大十倍,传染给身边的人。
对此,阿童木的评价是:永远长不大的小破孩儿。
对此,我的回答是:重阳中秋都不想爹妈,我要是你老子,非得大嘴巴子抽你。
关于童年的碎片回忆起来总是那么美好,以致于我很多时候都不太敢去回忆,特别是一个人呆在外面,举目无亲,看着别人热闹团聚的时候。在我们家乡,其实最应该团聚、热闹的节日并不是重阳,应当还是春节,其次中秋。但只要到了外面,“独在异乡为异客”,任何的节日都会成为思乡的理由。
小时候上课念课文,老师们总会饱含深情、声泪俱下地为我们讲述“乡愁”的概念,可惜同学们听起来却与鲁迅家的枣树无异,甚至还不如小蝌蚪找妈妈来得感觉真实。若要理解什么叫乡愁,根本用不着什么高深的解释与动情的泪水,乡愁与人生哲理有关,诸如“外面走一趟,懂得家里炕”、“少年不在家,在家不少年”之类的粗俗土话,远比那些貌似煽情的语言来得真实。当你一个人呆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饿得眼睛都花了,那些得理不饶人的主持人还在电视里笑眯眯地给观众介绍一盘热腾腾的水饺:“这是妈妈亲手做的。”这样的经历不用多,只要有一次,就用不着再去看什么《故乡》类的散文,自然就能明白, “思念的味道”这句小时候看来象是鸟语一般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记得头一年出外上学,离开父母还不到一个月,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无依无靠,与几个猪头同学在操场坐了整整一夜,几个人都想哭,但实在是没好意思把泪水放出来。之后的几年,我们都已经长大了,但还是不敢在节日里那么过,不是喝得酩酊大醉,就是互相把对方灌倒,领头的同学曾有名言:喝酒并不是为了消解乡愁,而是不想给乡愁制造机会。
再往后,工作后的生活更显单调,如果一个人孤身在外,对家人的思念更甚从前,一位北京的家伙某次还一半羡慕一半嫉妒地说道,你小子真好,在外面还可以体验到“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我听了忍了半天没忍住,脱口而出骂道:去你大爷的。
借助一段话来说:梁实秋写《雅舍谈吃》,并不能说明他就是个纯粹的吃货;鲁迅写《社戏》,也并不意味着他除了看戏就不去三味书屋读书;粗鄙如我,倘若写一篇《格调》,也并不说明我就能列入上等人的行列——我的意思是,就算我平时在爹妈面前一句表达感情的话都没有,也并不代表我就是冷血。那只是性格。
我经常见到有人什么事儿都不做,老大不小了还天天窝在父母家里混饭,然后用搽了老爹老妈的低档护肤品的手来指责拼打在外的人有多么不孝顺,做人有多么不道德,然后高呼可悲可叹。对这些人,我宁肯哭,也笑不出来。
第四部分 情圣泡妞第44节 谣言四起
CT扫描物质者,X射线也。
科普性的名词解释一下先。简单地说,X光就是一种能够穿透很多坚硬的东西的射线,类似厚如墙壁、泥土或玻璃者,人体当然更是不在话下。但玻璃和墙壁被穿就穿了,既不会疼也不会叫,但人就不一样了,除去那些非接受不可的,以此来诊断或治疗疾病的患者,要是有人天天跟那些嗖嗖乱窜的射线们打交道,危险性就会大得多。
我们就是这么一帮人。口腔科的医生每天是在掰嘴巴,肛肠科的大夫日日是在看屁股,而危险如我们者,则是陪伴着患者们接受那些令许多不明就里的人们谈之色变的X射线。需要说明的是,X射线纵使会杀伤人体内的白细胞,但偶尔的一次接受检查并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和伤害,换句话说,就是P事没有。就算是我们这些人,也会通过必要的防护来保护自己,比如说,防护墙门与合适的铅服。
“不管衣服是什么做的,都得厚点。”这句话是玉米说的,一个人高马大的中年男子,CT科的中坚力量,善良的老大哥,谬论的支持者。
就是这个玉米,医科大学的四年里,最大的心愿就是到“男生禁入”的女生宿舍看看。在北方,冬天是最容易伪装的时候,大四的最后一个冬天,他穿着肥大的羽绒服,戴着偌大的厚绒帽,戴上N层厚的大口罩,裹得像个孕妇一样,在几个女同学的掩护之下,终于混进了女生寝楼。到了女朋友的宿舍,他一甩帽子,潇洒地摘掉了口罩,如愿以偿、如释重负地说,哥们儿我终于混进来了,哈哈……
他还没哈哈完就被从门卫室尾随而至的看门阿姨的叱责声给截断了。阿姨的一句“别哈哈了,跟我下去”,玉米那个季度的奖学金就没了。乖乖龙滴冬,玉米纵使穿得象个包子,但还是被认了出来——他实在实在是太魁梧了。
上个星期的第一天上午,玉米象正常时候一样地坐到了操作台前,开始正常的工作。检查到第三个病人的时候,一个患者家属,三十多岁的小媳妇,走进了操作间,小心翼翼、陪着笑脸儿地跟玉米说:我能在这里呆一下吗?玉米没多想,点了点头,开始继续操作。时间在墙表中渐渐流逝,不一会儿,那个家属开始询问:请问,X射线能穿到我站的这里吗,请问,X射线能把血管里的血污染吗,请问,X射线是不是会造成什么疾病吗,请问,X射线……
玉米听了半天,回过头,没好气地告诉她:那你钻我后面得了。家属很感激地向他微微一笑,一出溜跑到了他的背后。但显然她还是有点不放心,不到五秒钟就挪一个地方,似乎是在寻找着最佳的位置,时而碰到玉米的背,时而撞到玉米的腿……
玉米终于忍不住了,回过头去,像传说中的狗熊一样咆哮:“你到底是来看病的,还是来耍流氓的?!”
比比谁无耻
我上中学那时候按理说应该是一个很傻的年龄,恐怕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都喜欢听范晓萱的“儿歌”,喜欢看琼瑶阿姨的小说,喜欢去电影院一起跟着李连杰揪心起伏——起先我还不知道那样很傻,“很傻”这个结论,是我长大以后由别人来告诉我的。
需要说明的是,那些告诉我诸如看琼瑶、听范晓萱是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