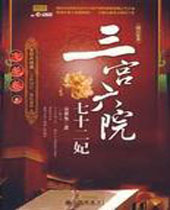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2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是那原先发自十八世纪巴黎的欧洲启蒙运动之延续。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末期,科学知识大跃进的结果。在新兴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人类学)光彩照耀之下,那原先的“造物主”(Creator)上帝的权威,整个动摇了。
可是上帝是今日所谓“西方文明”的总根;是白种民族安身立命不可一日或缺的精神源泉。上帝一旦不见了,则整个社会都要惶惶如丧家之狗,如何得了呢?所以他们在十八世纪这个所谓“理智时代”(TheAgeofReason),要把上帝、大自然和人类文明中新近才被解放出来的“理智”(reason)作个适当时安排。三造和平共存,相安无事,一个史无前例、光彩辉煌的近代西方文明,就在历史上出现了。
胡适所领导的中国启蒙运动,也正是如此。它不是受科学发展的影响,而是受西方优势文明挑战的结果。在占绝对优势的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那至高无上的孔老夫子的权威,也整个动摇了。
孔二先生那个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两千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适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朋友,你纵使是国学大师,你说孔家店不该打倒?你纵是神学大师,在新兴的“进化论”的科学论证之前,你还要坚持“人是上帝造的”?
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把孔家店打个稀巴烂,新的思想便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
“胡老师,本位文化真的就一无是处?”他的不疑处有疑的学生不免要怀疑一下。
“哪个民族,能丢得掉他们的本位文化?”
真的,十八世纪的欧洲丢不掉“上帝”;二十世纪的中国能丢掉孔子?把孔家老店要不顾一切彻底的破坏掉?孙中山不也说过“破坏难于建设”吗?打倒孔家店,只是个反托拉斯的运动,并不是要毁灭孔子。
果然,旧文化、旧思想,落荒而去。
新文化、新思想,就随著新的文化传播工具(语体文)排山倒海而来!
去岁余访沈阳“帅府”,见壁上斗大金字,歌颂张少帅是“千古功臣”。这就是《汉书》上所说的“曲突徙薪者无恩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的标准例子了。焦头烂额的张学良,怎能比得上曲突徒薪的胡适之呢?若论共产主义在中国之兴起,“千古功臣”应该是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啊!
水清无大鱼
可是胡适对他自己在文化发展上所作出的成绩,和历史发展中所负的责任,却一辈子也未弄清楚。他一会儿西化,一会儿现代化,一会儿又是世界化。说了数十年,说得不知所云。
记得四十年前,余尝把大陆上批胡之作,一篇篇地携往胡氏公寓,灯下与老师共读之,其乐融融。那些批胡之作虽多半都是“打差文章”,但亦不乏真知灼见的杰作。那时我尚年轻,遇有可诵者,我即以老师不牵鼻子之矛,以攻老师被牵鼻子之盾,和他认真辩难。适之先生为笔者所亲炙的最有容忍风度的前辈。但是他也是一位有七情六欲的老先生;我们师徒所见亦每有不同,而我学习的态度又十分认真——不被说服,即不愿苟同。所以有时老师也有几分恼火。他不喜欢一个学生,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批胡者助阵嘛——这也是胡师很可爱而不矫情的地方。
本来嘛!一位开创宗派和山门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宗教家像孔子、老子、墨子、释迦、苏格拉底、耶稣、穆罕默德、马克思、杜威等等,他们成佛作祖,往往都是无意间得之;甚或出诸百分之百的偶然。他们生前也往往不知道自己“一辈子在搞些什么”?这句话就是适之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夫子自道”。老实说,这也是我这位弟子在“夫子自道”中,所发现的百分之百的真理。
耶稣这个小犹太牧羊仔,生前哪知道他死后合搞出个那么伟大的宗教来;两千年后他的生日派对,还那样风光?穆罕默德根本是个文盲,造反有理,当了皇帝。但是他又怎知道他那些文盲之言,后来竟成为穆斯林文化的总根呢?
以上所说的是宗教。再看比宗教更有力量的马克思。马老在一八八三年入土之前,就抵死不承认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今日世界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老了,动不动就说他要去见马克思。真要见了马克思,可要当心老马的拐杖呢!
总之,成佛作祖的思想家、宗教家,都是圣之时者也。他们是站在各自时代的尖端的智者和贤者。按照时代的需要,以言教身教来推动或逆转他存身的社会发展。但是他们思想和信仰的成长的程序都是复杂的;他们思想的效验与影响亦有赖于历史前进中的长期实证,因此水清无大鱼,人类历史上任何宗教和文化的巨人,其思想体系都是朦胧难辨的。他一旦捐馆,弟子信徒和新仇旧怨,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因此儒分为八,墨别为三,佛有十宗,回有两派,耶有百种,马有千家了。
胡适这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跳不出此一通例,因此当他在逐渐向历史海洋下沉的今日,他的思想体系、学术贡献、影响大小、功过何在,也早就言人人殊了。
而今而后,批胡者固早有百家之先例;而研胡继胡者,各觅师承,也寻之不尽了。
“一国两制”和“半盘西化”
再者任何思想家都是主观的;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因此他对他自己思想的历史背景很难有客观的认识;他对他自己加于将来社会的影响,也绝对不能逆料。——胡适也是如此!
举个切实的例子来说吧:胡适言必称杜威,称了一辈子,为什么结果在中国反搞出个列宁来了呢?这是他所不能逆料,也不能提出合理解释的地方。但却是我们今日要提出的“启蒙后”(Post…Enlightenment)的问题了。
须知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从中世纪的东方农业社会的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工商业的社会型态),实始于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之签订。但是你可知道〈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六年,一八四八年,欧洲又出了个〈共产党宣言〉(TheunistManifesto)?
〈共产党宣言〉意味著什么呢?〈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欧洲中心主义”分裂的开始。远在文艺复兴的初年(一三〇〇以后)和宗教改革的高潮(一五二〇),欧洲的文化与思想,区域性已十分显著。在十九世纪中期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分裂时,多少也是按老区域划线的。
不幸的是当欧洲文明日趋分裂之时,也正是我们中国西化运动逐渐加深之日。结果呢,就在我们决定搞全盘西化之时(一九一九的五四运动),也正是他们彻底分裂之日(一九一七的十月革命)。
试问我们搞“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们(胡适和陈独秀都是),现在“西化”一分为二,你们也只能搞“半盘西化”了,你搞哪一半呢?
胡适选择了杜威。
陈独秀选择了列宁。
两位老友分道扬镳,《新青年》也就变质了,“启蒙后”中国也就一分为二,“一国两制”了。
——一国两制是从一洲两制开始的。
所以“一国两制”不是邓小平发明的呢!它是胡、陈二公根据“一洲两制”首先搞起的。只是胡、陈的模式是个你死我活的模式:“既生瑜、何生亮”的模式。邓公的模式则是个和平共存,“你死我做和尚”的模式罢了。
朋友,不是瞎说吧!七十年来的中国悲喜剧,便是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在中国斗争的结果。一九四九年列宁把杜威打败了。这项胜利的代价,据中国之友的史诺先生所作的最低估计是人头六千万颗啊!其后三十年发生在大陆上各项政治运动,还不是解放前“一国两制”斗争的延续?只是到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之后,邓公才把这桩“扭转了的历史,再扭转回来”。
胡适之和陈独秀搞一国两制,一分为二,分了七十年。如今在邓氏指导之下地下相逢,又可以合二为一,再办其启蒙后的《新青年》了。
也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近十五年来,海峡两岸社会转型的速度是惊人的啊!按我们在海外所能读到的数据,十五年前从零开始,大陆上的私营企业中,个体户今已增至一千四百万单位;集体户亦有六百万之多。其他如外贸的发展和总生产的累积,人均收入的提高,都是史无前例的。
笔者在资本主义国家教授资本主义历史,前后凡四十年,如今翻翻陈旧的教科书,对比一下手头崭新的数据,我还没有发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有过像今日大陆上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呢!我应该告诉我的学生们,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还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呢?按社会科学的定义,它应该是后者。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远景来看,则二者都无不可。
但是如此发展下去,中国就不姓“社”了吗?非也。君不见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季的“镀金时代”(TheGildedAge)搞了一段很短的金权政治之后,一进入本世纪,它的资本主义就开始修正了?二次大战后,美国已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许多主要的优良制度,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美国将来的问题是在社会道德之崩溃,和法律制度之瓶颈。它自动调节的经济制度,无膏肓之疾也。
所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大陆经济如不节外生枝,则问题不大,而且顺利发展,必能合二为一,融社资于一制;拉平沿海与宝岛的差距,而引导两岸的政治合流。
台湾今日“金权政治”的发展,原是一百年前美国“镀金”的模式。等到黄金不能左右选票时,它就会烟消云散。
因此今日海峡两岸的前途多半仍决定在大陆。大陆如经济与政治平衡发展,则一百五十年来的“转型运动”,很快就会合二为一,进入“最后阶段”。制度出现“定型”,则百年盛世,东风压倒西风,也是预料中事,不算是什么奇迹了。
不过,将来社会的定型,今日在地平线上虽已颇见端倪,但是历史发展毕竟因素繁多,中途转向,再兜几十年的圈子,也不算意外。只是当前两岸掌舵者能多一分远见,少一分私心,则最后十里应该不难渡过。只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翻车多在家门前,究不应掉以轻心罢了。
“启蒙后”的显学
本篇之作的原始动机,是为吾友欧阳哲生教授的大著《胡适思想研究》,写篇序文。如今下笔万言,未提欧阳一宇,岂非离题千里哉?笔者之所以如此做者,正是看中吾之小友这篇论文的重要性,所以才不愿草率下笔,敷衍了事。
我个人觉得,胡适思想研究,今日在海峡两岸既已逐渐解禁,按照压力愈大、弹力愈大的力学通则,它今后必成显学无疑!杜甫大师说得好:“汝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胡适是中国文化史上照耀古今的巨星,岂是暗探特务所能禁绝得了的。但是“胡适研究”这门显学,在下世纪的发展,又有个什么样的趋势呢?记得往年胡公与在下共读海峡两岸之反胡文学时(那时在大陆上叫做“反动学术”;台湾叫做“毒素思想”),胡氏未写过只字反驳,但是也未放过一字不看。他看后篇篇都有意见。只是当时没有袖珍录音机,我没有把话录下就是了。大体说来,他对那比较有深度的文章的概括批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胡适是位很全面的通人兼专家。他的专家的火候往往为各专业的专家所不能及。所以各行专家如只从本行专业的角度来批胡,那往往就是以管窥豹、见其一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为通人所笑,认为不值一驳了。
最糟的还是胡适死后,他的遗嘱执行人年老怕事,任人乱挑学术大梁、妄下雌黄,不特使佛面蒙尘,也把个活生生的博士班导师,糟蹋成“春香闹学”里的学究,实太可惜。这些都是文化史上的不幸,今后不会再发生了。可是新兴的胡学又将何择何从?有一次在他公寓里,我记得胡氏兴致甚好,向我大谈民国政治。他表示对“民初国会”之失败深为惋惜。因为那些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他又对国民党没听他话去“一分为二”,表示遗憾。否则中国当时不就有两党制了吗?听后,我嬉皮笑脸的反驳他说:“胡老师呀!您提倡的抽象学理,无一不对;您所作的具体建议,则无一不错。”胡公闻言颇为光火,大骂我“胡说、胡说”。但他还是留我晚餐,餐后还和我这位学生清客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