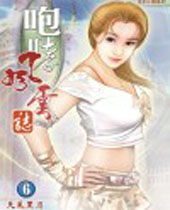映城志-第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沧东的《绿洲》不同于司空见惯的爱情电影,因为在他的镜头底下挣扎摇曳和舞蹈的,不是俊男美女,而是残疾人,或者说是被上天不公平对待的生命物种。在所谓的正常人眼中,他们的生存等于心脏或者脉搏的跳动。所幸的是,李沧东并没有用他的镜头满足所有人的猎奇癖好,也没有抒发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边缘关怀。他掠过残疾人和修车工的形之上——在一个人际关系普遍淡漠的社会,即便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正常人,如何面对外界进行表达?
将军带着公主出席母亲的生日宴会,被一家人冷嘲热讽地赶出来。在酒店门口,公主坐在轮椅上不说话,将军问:“你为什么不高兴啊?你在埋怨我吗?天这么冷,我们走吧!……好吧,你不走,那我走了,我再也不管你了。”然后是一个远景,凄清的广场上只剩下独自坐在轮椅上的公主,没有人可以看到她此刻的表情。
……这是《绿洲》中非常让人伤感的一个细节:过了一会儿,将军又转回来,跳着舞站在她面前。然后两人一起去唱卡拉OK。将军把麦克风放在公主的唇边,任凭配乐空响。这个细节的颤音一直延续到将军背着公主踉跄地跑入地铁站,配乐停息,公主为将军清唱了一首歌——或许,这一幕只是一个超现实的梦境。
看他的电影,让我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日渐衰老的城市,每天做着无数机械性的重复劳动,说着大量言不由衷的话,在冬日抱紧自己的双臂,在春天来临之前抹净室内的尘埃,而且从未如此迫切地渴望一场爱情。
遗憾的是,这种超现实的梦境,在他的另一部作品《薄荷糖》中,被逼进了一个对人性彻底绝望的死胡同。
孤独频盗七
张允铉的《伤心街角恋人》(又名《上网》)、金正权的《同感》、李廷香的《美术馆旁边的动物园》、朴钟宰的《美丽的日子》等,都是以细节动人的爱情电影。
在《美丽的日子》中,大学期间服完兵役的男主角君浩说:“我没有方向,从不去爱;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心里很乱。只是记得自己曾经骑着自行车,并看到街角栅栏边突然跃出来一只鹿,而鹿正望着自己的情景。”这只鹿,到底是梦境还是影片暗示的一种象征意义呢
?对被这种情绪深深感染的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来说,像君浩那样,与有妇之妇偷情纵欲,或者与大学时代的恋人纠缠,最后似乎又爱上昔日恋人的妹妹……似乎都不能排遣心中的孤独感。直到看到开洗衣店的老君浩画的画,才稍微觉得踏实。那张画用炭精笔描绘着对面街角的建筑,在建筑的前方,是老君浩自己添加进去的植物。
生命的消解过程,总是像一条由强到弱,又由弱到强的曲线。正如昆虫那样,为了快快长大而争取每一份食物和养料,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开始厌倦这种自然法则,甚至想让自己学会冬眠。春天到来,苏醒之后,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换了一副身躯,只是突然热爱上活着的每一种细微感受,又复忙碌。
有时候,要阐释生活中重大的哲学命题,或者构筑一部博大精深的思想性电影,恐怕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吧!大而无当,是每个雄心壮志的导演很容易撞船的那块礁石。看似简单,却可以见森林,这种扎根东方的美学体系,对于电影,或对于日渐浮躁的城市生活,还是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救赎作用吧?
香港
明明不是天使一
香港的魅力,不在于置身厚盾襁褓中的母语魅力,而是一种荒岛求存的再生魅力。它吸收养料如一只巨大的海绵体生物。从英国文化那里吸收了英伦摇滚、青少年次文化、新机场客运大楼和新九广铁路客运站;从美国那里吸收了好莱坞、迪士尼主题公园、Hip…Hop、Jazz…Punk、贝聿铭的中银大厦、SOM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从东瀛那里吸收了卡拉OK、日本跳舞音乐、安室奈美惠的染发、滨崎步的豹装、HITOMI的男式内裤、手提电话、数码相机、曾风靡一时的电子宠物Tamagochi、港岛的铜锣湾和九龙旺角商业区的日式的百货公司、《游园
惊梦》或者《我爱厨房》或者《不夜城》……中的日本艺人(哈日同时也被日哈),如《悠长假期》最后一幕的山口智子,穿着婚纱奔跑在波士顿的大街上(这本来是属于香港爱情片的经典镜头); 还有从韩国那里吸收的K…Pop、韩剧、韩国街(金巴利街)、尖沙咀新港中心A6张柏芝时装店(韩国时装品牌“A6”以其花哨艳丽夺得港人眼球,更甚日本的20471120)、猪蒙眼“贱兔”玩偶、金马伦道的“草苑”和美丽华中心“新罗宝”的“正宗韩国料理”……
但是香港的魅力,也形成了它的隐患。因为吸收速度迅疾,刚刚流行的旋风还未停息,另一股飓风又已经来临,像沙漠中的沙砾,“风”成了雕塑师,不可确定性和变幻莫测成了“主题”,浅藏在沙砾底下的任何思潮都根本来不及巩固,也找不到安全地基,就行将摧毁。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两生花”、“香港部落”、“音乐传讯”等独立厂牌推出的唱片里,虽然Sample技术或者其他手段的电子(音乐)技术完全合乎潮流,但是听起来却像是“扒带”音乐;为什么在谢霆锋、冯德伦、夏永康等青年新锐导演那里,看到的只是“实验电影”的几缕羽毛,而香港业余MV自拍大赛作品《神经花园》还忙不迭地向羽毛“致敬”。
梁文道:
所有外来的潮流文化、流行文化来到香港,就变成了一种彻底装饰性的潮流。人们去RAVE PARTY,并不是因为RAVE PARTY里有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感觉,他只是想,我身为潮流的一分子,怎么能不去RAVE呢?……香港是一个非常追逐表象的社会,它很单一,单一到只追求表象,整个社会只往同一个方向去,所以,香港的夜生活也很单一化。你跟台北比,台北有通宵的书店、通宵看漫画的地方,嗜好很多元化,但是香港不会的。在香港,你从来只能讲机会,我不能说我永远坚持做牛仔,只能说这一阵子大家流行牛仔,我就搞牛仔这一套,要看准时机,过了半个月,不流行牛仔了,我就要另搞一套,是这样的。香港人的执著,是执著于别人怎么样看他。西方的潮流,在流行热潮过去之后,还会有一批人,数量不大不小,还会坚持那个潮流,比如朋克,今天一点都不流行了,可是英国还是有些人,就是朋克,永远朋克下去。但是香港不会的,因为过时了,过时就会被人笑,他很怕被人笑。
而且,香港的年轻一代丧失了一种东西,就是嗜好。你问他们,现在喜欢什么?他会说,喜欢打机(电子游戏机),喜欢唱卡拉OK,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喜欢睡觉。但是,这些是嗜好吗?嗜好的定义,不只是某种发泄,它对人的要求很高,要有某种坚持、某种兴趣、某种因兴趣而来的长期关注和发展,它会成为一种学问。十几年前,还会发现许多年轻人集邮、野外宿营,他们有这种嗜好,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种人越来越少,兴趣越来越单一、越来越浅薄、越来越同质化。前一阵子流行过集邮,但不是因为嗜好,而是因为流行,有几张邮票炒得很贵。看漫画很流行,但它也可以是一种嗜好,外国有些漫画迷很专业,到处去搜集各种版本,香港不是,看漫画的人很多,出了一本什么新漫画,大家都去买,但是看完就丢掉了,从不去问那些漫画到底是什么意思。香港的年轻人越来越浅薄,而且是一种集体性的浅薄,大家越来越像、越来越一致。香港也越来越单一,越来越缺乏个性,越来越成为一个一元化的社会。
……又或者是因为香港人的现实性,在这个生存法则尤其鲜明、尤其讲究效率及回报的城市,人们上紧发条,就像《麦兜故事》中那只小猪的妈妈麦太般:
一定得!一定得!多劳实会得!唏!
人肥就更加要醒目。
多劳多得,多劳多得,多劳多得,搏命做!
人穷就更加要醒目。
要用两手搏命lar,
人穷就更加要鼓劲。
多劳多得,多劳多得,多劳多得,搏命捱!
……
脚步自动形成一条循环流动的纽带,一个跟着一个,不敢怠步。这种感觉在乘坐香港地铁时尤为强烈,人们总是在奔跑,车门行将关闭的时候总是会最后挤进来一个人。似乎如果突然停止的话,就会有人变成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刊登在报纸上的那些“数字”。同样的压力,较之港人会显得颇为沉重(比如说非典时期,香港政府委派心理医生指导病人防止其自杀)。金钱的重要性体现在香港因人口密集而诞生的凸窗(凸窗曾像早期的笼屋那样,是最有香港特点的一类窗户,它的窗台曾作为儿童的“卧室”)、“钻石”形平面、“剪刀式”楼梯、空调机窗板上,伴随着成长中的视野变换。
在这种视野下,诞生了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比如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在港九新界11所津贴中学进行的一项有关青少年偶像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七成被访者心目中的偶像,首先是本地歌星,其次是电影明星和电视演员—就不足为奇。香港作家西西在《浮城志异》(1996年,青文书屋)说道:
只有到过浮城的人,才知道浮城的镜子,是一面与众不同的镜子,只能反映事物的背面……当浮城的人照镜子的时候,他们要照的往往不是自己的脸面,而是脑后的头发……
此段话不失为对一个潮流飞逝的城市,最准确的概括。
她的一切,都是即时性的。比如她的手表上的时间—1960年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
—王家卫《阿飞正传》
就像她盛产的“天使”,很漂亮很新鲜,但总觉得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放在太阳下面,很快就要被热气熔化掉的样子。
明明不是天使二
《中国盒子》剧照
所以香港电影的最大特点,就是首先追求巨大的商业回报。在香港经济最澎湃的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商家制造如火如荼的造星运动、电影繁荣以及浮躁的市民心态,这个心态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电影业像一个超市。超市总是被制造为膨胀发展的城市中最中坚、最贴近市民生活愿望的消费加速器。它融会了种类繁多却大多缺乏个性的商品,在一个冷空气弥漫的巨大的集装箱里面购物—一只汪洋大海中航行的集装箱,每一种商品(电影)都像一只只彩色的水雷式浮标,代表着从草根平民到中产阶级到超级富豪的海上花园,买座的人拖
着一只篮车走进来选购,银幕按照不同类型纵横上下格格划分。它的中央空调及良好的密封性,淡漠了人们对窗外世界的真实记忆。拖着篮车的把手,仿佛拖着一种自己不会轻易觉察到的臆想症生活。
这些具有超市货品般的特性的电影:毛巾、高钙牛奶薏米饼、一品料理、咖喱酱、冻干香脆蔬菜、卡西欧塑料手表等等,因为简单、实用、轻松娱乐、易于理解、口味适中,曾经是大众日常生活的作料,像八卦报纸或者芥末。稍有异味的,买的人少,超市经理也就陆续减少货源,或者放在少众柜台,少众柜台的存在,不是因为它必须存在,而是一种时尚。
遗憾的是,这个即使是超市般的大众口味的电影市场,现在亦人潮冷落。
华裔导演王颖在他的一部语焉不详的电影《中国盒子》中,称香港是庞贝城。张曼玉脸上那块疤,像巫师的镜子,仿佛预见这个城市将经历一场公元62年的大地震。所不同的是,《庞贝末日记》昭示着意大利电影的新生,而庞贝的香港,却暗指香港的电影工业乃至文化艺术领域的一场沦陷。
且不谈这部拍得粗糙的滥片以及话语中那个拍摄记录片的英国摄影师所经历的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式的失落。但香港电影业工作者总会在2002年的公开函如此呼吁:“目前本地电影业已陷入危急存亡之秋,业内有七成人士失业或半失业,电影产量由全盛时期一年的300部,下降至今年上半年不足30部。”……“2002年暑假黄金档期的票房总收入仅为1。5亿多元,较2001年同期下跌逾四成。”……“电影院不得不推出减价、免费停车或送礼品等救亡运动,挽救惨淡的香港票房。”—用“庞贝”形容这个东方的好莱坞并不过分。
人们选择一种电影或者观影方式,是来源于其价值观念:在一个节奏和速度飞快的城市中,人们会选择“一种不需要太多时间就可以看完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