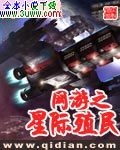�ձ�ֳ��ͳ��̨����ʮ��ʷ-��3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ӵ���ַ�Ȩ������ɱ��ᣬֻ�����ҹ��Ҵ���Ȩ�ķ�Χ֮�ڡ����پ�־��֦�����վ�ʱ��̨���ܶ�������ެ���ߡ�����Ӣ�ó��棬̨����1997����156ҳ���ֵصĽ���õ���һ���̶ȵIJ��ɡ�1903�꣬�ܶ����ƶ�����ެ��١�����һ����ެ�ˡ�����ެ�ء�ͳ�龯�챾���ƹܣ��ڶ�������ެ������ָ̩���壩����Ϊ��������ެ������ָ��ũ���ޡ����塢���������������ϡ�³�����壩�Ը�Ϊ�����������ԡ���ެ�������߰�Χ����֮����һʱ�ڵġ���ެ���ߡ��У�����ν����ެ���ķ���������֮�أ��ھ��Ѱ����ϣ�����ެ����Ӫ��Զ���ڡ���ެ����Ӫ�ѣ��ں��������ü�����̫ʱ����1906��1910��5����ҵ�ƻ��У�ǰ���ܾ���Ϊ19379414Ԫ������Ϊ260000Ԫ����Ȳ��ߴ�74�����ϣ����¼����롶̨��ެ��־����̨��ʡ����ίԱ�ᣬ̨����1957����711ҳ��ͬʱ�������ܶ�����ԭס���������˽ϴ��ת�䣬���Ӿ�̨���ڵĸ���ת����ѹ���ܵ�ԭ����Ϊ������ձ�ֳ�������ɽ����Դ���Ӷᣬ������ǿ�ֿ���ԭס�����Խ�������1903��1904�꾯�챾��ެ����顱�ϵõ�ֱ�ӵ����֡������ž��Ǹ��ذ�������ɽ���ƽ���ͨ��ɽ���ĵ�·Ҳ������������������
����������̨��ԭס��Ľ��������ֳ���ֳ���ߵIJб���һ�棬����������������������Գ��ݡ�ެ�ˡ���ɱ���ۣ��������졢���ºͱ�������ɽ��Ҫ�������ɱ��ެ�ˡ�������ɱ��ͷĿ�ߣ�����100Ԫ��ɱ��ެ���ߣ�����50Ԫ���������¼��أ�����˽���������������̨����ɱ��ԭס���Դ�����̨��̨֮Ŀ�꣺��������
��������������ʮ����������������ǰ�ɽ�����ߵ�̽��֮�ʣ���������һ����ʮ�֣����Ҳ���ǰ��Լ���ٹ��ߴ�������һ��ެ�����������ˣ������������֧������ɽ���ල��̨�������β������������������ᆵ����������Ӧ�ȵ������롣�ʴ���DZ��������ʮһ�����ߴ����������һǹ�ᴩ��������ʹ���ж����ѣ�������ͼ���ߣ������Ⱒ���ֲ���һǹ��ʹ�����浹�¡���ʱ�������β���ȥ����ެ����Я��ެ����������������������
�����������ϳ����¸�֮�ж�ʵ�����Ŀ˾�ެ�羯��Աְ֮�𣬷��ϰ䷢�����й�����֮��ѵ��һ���ڶ��ţ�����������й����¡���ѧ�£�����ɱެ�͡�֮�о��������������Ϊ��������������̨���ܶ�����������ѧ�����ֻ����ļ�����̨��ʡ����ίԱ�ᣬ2001��
�������֡���ެ���ߡ��ij�����3��
������������ԭס��ȿ������κμӺ����˵���ͼ��Ҳû���κι�����Ϊ��������Ϊ����ԭס�������а�ެ�����������֮�֣���֮������ǡ���������
�����������ü�����̫��̨���ܶ���ԭס�����������ǿӲ��������ʼ�����ı����ԭס����������ѹ���ˣ�������ˡ�������ެ�ƻ������üƻ����ȼ�ǿɽ�ص�·�Ŀ��أ������˹ᴩ����ɽ���ϱ��İ����ߣ����������ձ����ᾯ����ԭס��ͷĿŮ������������ڲ����������¼��ķ����������������ذ������ƽ��ġ���ެ���ߡ���Ч�����ʶ���������ެ�ƻ�����ȡ�����ж�ǿ����ѹ̨��ԭס���������ƶ�ɽ����Դ�Ŀ������̡��������Ͷ����̩����ԭס����ַ��ж����͵ط�ӳ���ձ�ֳ���ߵ�����ת����̣�������ʮ����ʮһ�£�������һ�ݵ����гƣ���������
������������Ͷ��Ͻ����ԭס��Ⱥ����С����ʮһ�������߰���ʮ���˿���ǧ�Ű١�����ƾ�ѵ���֮�գ��ư��Դ������������������ǰ�����������Σ�����ʱ֮��ԭס�����ߣ�ר�ɻ������壬�ں�ƽ��ʵ��ǰ�������ߡ�Ȼ����������ʮһ�������������֮ɽ�䣬�����о���Ӫ֮���ӣ�ʹ�����ܼ���ȫ��֮����ʱ֮���Σ�������δ����ʱʱ��ʾ�䲻ѷ̬�ȡ��˴Σ����Ⱦ������֮����Ա�����������棬���¼�������������������֮���Ϯ����弣���ɱ������Ա�ȣ�ǰ���Ѵ�����Σ���������¶������Զ��������ѣ�����֮״���������ء��ʹ黹֧Ԯ��������֮����Ա���Գ��ر�����һ����Ŭ��ƽ��ɽ�����ƣ�Ȼ��ʮһ��ʮ�������밯����Ϯ����弣��⾯����֮Ѳ�鲹������������һ������������һ�����ˡ��������ڼ���������ԭס�����֮����ͷĿ���������Σ��ʽ��������ھ���Ա������פ����Ա����Ѳ�鲹����������ԭס��׳��ʮ�����ٽ����֮���壬������ֹ�����밯�����ڶ����¶����⿳ͷ�ȣ���Ű��������֮���ھ�����ǰ���Ҫ�ع����������£��Գ���϶����֮�ơ������Ҵ˰��������ƻ���üϪ��һ�������ر���ɽ�Ÿ�������ׯ��Ϊ������������֮�����֮��������֧��Ͻ��֮�ΰ��������������ɡ�̨���ܶ�������ֱࡶ��ެ־�塷���ν����롶�վ�ʱ��ԭס������־�塷���ڶ������¾�����̨��ʡ����ίԱ���ӡ����Ͷ��1999����133��134ҳ����������
������������������ƣ��ձ�ֳ�־���ǿ����̨��ԭס�����ѹ�ж����ı�ԭ�ȵĻ������ߣ�ת�Ծ��¼���ѹ������ɽ�صġ�ެ�ˡ���̨��ԭס��þ�ɽ�أ������������ǵ���Ҫ���ʽ����˸�������д�����������ҩ��Ҳ����ƾ������Щ��װ�������ܲ������ձ�ֳ���ߵ�������ձ�ֳ���ߵ�������Σ�յģ��Ƕ�̨��ֳ�������DZ����������ʵ����в��������̸��̫³��ԭס��ʱ�ͳƣ������䣩׳����ǧ��δ���˲���ǹ���Ҷ����������������������һ�����ҿ��ܹ�����ݱ����������̨���ܶ�������ֱࡶ��ެ־�塷���ν����롶�վ�ʱ��ԭס������־�塷���ڶ������¾�����̨��ʡ����ίԱ���ӡ����Ͷ��1999����373ҳ����ˣ�̨���ܶ����ھ�����ѹ��ͬʱ����չ�˴��ģ���ս�ԭס��ǹ֧��ҩ��ȫ�����ж�����ެ���ܳ������ƣ����ڴ�����������֮�⣬������ѹ����ͼ�ƽ���ެ��ҵ�����ڱ�ެ����ѹΪ���������֮��������ެ���Ի���Ϊ������ѹ��֮��Ȼ����ѹ�������������ż���ʵ�У�������Ч�����������ߣ��ิ���ǡ�����Ϊ���ȶ���ҵ֮Ŀ�꣬�������о��������Ϊ�����ں�ެ������֮ǹ������ެ�˲���ǹ������ެ�������£���֮��ǹ�������У���һ����˳������δ��ȫ�ţ���δ�ɳ�Ϊެ����ƽ������ǹ��ʵΪ��ެ���Ƚ����⣬ǹ��֮���ּ�ϵ��ެ��֮����Ҳ�������¼����롶̨��ެ��־����̨��ʡ����ίԱ�ᣬ̨����1957����729ҳ�����ü��ܶ��ƶ��ķ�����ҲҪ����Ѻެ��ǹ��������ȡ��ҩԭ��֮��˽�����¼����롶̨��ެ��־����̨��ʡ����ίԱ�ᣬ̨����1957����745ҳ��ǹ֧��ҩ�սɻ��̨��ɽ���ձ�չ�����ݲ���ȫͳ�ƣ�1902��1930��乲�ս�ԭס��ǹ֧28900��֧���ӵ�49000�����������ν��������ެ�ƻ����ڼ��սɵľ���22958֧��ռ������������¼����롶̨��ެ��־����̨��ʡ����ίԱ�ᣬ̨����1957����745ҳ�����ݡ���ެ־�塷��������ެ��ҵ����ƻ���Ϊǰ���ܶ����ü䲮���������Ǿ�������Ȼʵ���ߣ����ѹ���һǧ��������Ԫ�����˶�ǧ�������ˣ���Ȼ��ʧ���أ����սɻ�������һ���ǧͦ���ص�ԭס��������ǣ���νǧ�ź����˿��١������������й��ս�ǹ֧��ͳ�����ֳ��룬�����������е����ݶ�ǹ�ܵ�ͳ��δ�������ڡ��������������ս����Ϊ���������±�5��1��ʾ����������
���������ܵ���˵���ձ�ֳ���ߵġ���ެ���ߡ����������ߣ�����ѹ����ν�ĸ���������ѹ���棬����������ϵ����Ͼ��ӣ���̨��ԭס��ʵʩ��ѹͳ�Σ�ͬʱ��Ϯ����İ����ƣ�����̨����̨��Ϊ������ԭס��ķ����������ս�������ҩ��Ϊ�ձ�ֳ���߶�̨��ԭס����ѹ�����Ҫ������ڡ����������棬�ɷ�Ϊ������Σ������Ƕ�ԭס��������������ڲ����ʹ͵ȣ��ټ���ɽ�ص�·��ˮ������������٣���ͼ���ԭס���������˼�롢��Ϊ�������������ת��Ϊ�ձ���ʵij���˳��
�������֡���ެ���ߡ��ij�����4��
���������ձ���̨֮����ֳ�ּ��൱���Ӷ�̨��ԭס�����ν����������������Ϊ������ʶ��̨��ɽ�ؾ��Ƶ�ƽ�ȼ�ɽ����Դ�Ŀ������벻����ԭס����ձ����������Ҫ�ڣ�̨�壩ɽ��������ҵ������Ҫʹެ�������������ʹ�����������;������ȴҰ�����������پ�־��֦��������ʱ��̨���ܶ�����ެ���ߡ�����Ӣ�ã�̨����1997����7ҳ���ձ�ֳ���߷�Ч����ĸ����ƶ��������ĸ��Ѿ֣����Ǵ��¸�ѹ֮����ձ�����Դ��ݨ���Ѿ�Ϊ�������������ڸ��������ѻĵء�����̨����������������֮��ѧ�ã�����ެ���ӵܣ�ʩ�Խ̻�����ȥ������֮�ģ��ױ�֮�ף��Ա����׳������������������¡�ʳ��ס������������Ǯ��ެ���������־֣���ϲ��֮���̸����˵��ʱ�����������跹���⡣�����������ϲ�����ض��ã����˶�ȥ���Դ�һ��ʮ��ʮ���٣��ഫ��ȥ��Զ���������˴��÷����л���˳�����پ�־��֦��������ʱ��̨���ܶ�����ެ���ߡ�����Ӣ�ã�̨����1997����8ҳ����ʵ������С��С�ݽ��е�����������������һ�����ϣ�����չ�˸��߳�Զ�滮���ڲ��ƻ�����Ŭ���ı�ԭס��Ĵ�ͳ������������ϰ�ߣ��������ǽ���ũ����ҵ�������ھ�̨���ڻ��ڲ��ֵ�������ţ���������飬�Դ���黯����������
���������ڲ���ϴ��ģ��չ������1910�������Ҫ�Ļ�����ˮ��ָ����������ָ����������ָ��������������ѷʼ�����ָ����������ָ��������ҵָ���������ֹ���ָ�����ȵȡ�ԭס��ĸ����ƶ�ԭ������ԭʼ�ַŵ�Ǩ���ָ���ʽ������ƻ���ɭ��ֲ�����������ˮ����ʧ������ֳ��ʵʩˮ����������ƣ�ԭס���ˮ�����������˽ϴ�����ӣ�1923��Ϊ531�ף�1930����Ϊ1350�ף�ÿ��ƽ���ջ���Ϊ9346ʯ������ҵ��Ҫ��ˮţ��ɽ��������������ˮ����ֲҵ�ķ�չ��������չ��������һЩ�����ֹ���Ʒ��������������ɽ��ԭס�����ɫ����������ķ�֯Ʒ�����塢ľ��ȣ�������˲�����Ľ���еĵط�������Ǩ��ԭס��ת�������滷������O4500��Ԫ���������³ǵ�ԭס��720���˼���Ǩ������������
���������վݳ����ձ�ֳ�ֵġ���ެ���ߡ������¿ɷ�Ϊ�����Σ�һ��1895��1901�꣬������ƽ����ѹ�����������װ���ն������ԡ�ެ�ء����л������ߣ��Ա㽫̨������ֶ���֮���������ƣ�����1902��1909�꣬���ں�����װ�λ�������ѹ���ձ�ֳ�����ڳ�������ԭס���ȡ���ƣ�һ���ƽ������ߣ����ž�����������һ��ӽ���ν�ĸ���������ͬʱ��չ��ެ�ء����飬�˽�ԭס�������״����Ϊ�ƶ����ߵIJο�������1910��1915�꣬ȫ����ʵ��ѹ����ެ���ߡ�������ν��������ެ�ƻ������Ծ�����Ͼ��죬��һ���ƽ������ߣ���չǹ֧��ҩ�ս��ж����ձ�ֳ������̨��ʵʩ�ġ���ެ���ߡ���һ���ص㣬���ǽ�ԭס���뺺�˷ָ�����������ԭס��۾ӵ��������ƺ���������ԭס��֮��Ľ�����ԭס��������ɽ����������Ҳ�����������ԭס��������ձ��˵�������ԭס������Ұ��״̬������ʢ�У�Ϊ��ȫ��������Ѷ�Ϊ֮����ʵ���ϣ��ձ�ֳ�����������Ǵﵽ��һʯ�����Ч�������ȣ����Ϻ�����ԭס����������ձ�ֳ�ֱ����Ծ��÷���ѹ��ԭס��������ͬʱ����̨���������Ͽ��ն�������Σ�̨��ɽ���̲��ŷḻ����Դ�����������Ʊ�������̨�屾�������ʱ��Ľ��룬�ḻ�ı��س����ձ�ֳ�ֺ��ձ��ʱ��Ķ�ռƷ�������Է��״̬Ҳʹ���ձ�ֳ�����ܸ���Ч����ɽ�ؽ���һ���������ġ���û��������Ⱦ��ͳ�λ�����������������ν����ެ���ߡ���ʵʩ�����⣬̨��������˽�������̷����ȣ����������ڡ�ެ�ء���ʹ�ó�Ϊ��ͨ�����������������������ެ�ء�����Ȩ����Զ����ƽ�أ����ΰ���ȡ�ޡ�������һ�㾯�������⣬�������ԭס��Ľ������ڲ��������ȵ�����������ָ������̨�塮ެ�ء��ľ��죬���Ǿ��죬ͬʱ���ǽ�ʦ��ҽ������Ϊ��������ָ���ߡ�����������µļҳ����������ģ���̨�徭��ʷ����������̨꣬������963ҳ���Գ��ձ���̨ͳ�εľ�������ɫ�ʡ��վ�ʱ�ڵ�̨��ɽ����ᣬ���γ��˽������͵�Ȩ���ṹ���߸����ϵ����Ծ���Ϊ������ֳ��ͳ���ߣ����Ϊͷ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