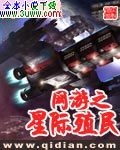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2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干部开办讲演会,动员无智的民众,名为欢迎,鸣放鞭炮,进行一种变相的示威运动,有时则召开旁若无人的大欢迎会,一壮气势。干部们对地方民众的这种态度,颇为自得,以志士自居,一味煽动起民族反感,不加省察,以致造成空前的反母国风越发加深。” 若林正丈:《台湾总督府秘密文书“文化协会对策”》,(日本)《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创刊号(1978年)。在这当中文协干部无形中成为集聚民众的领导者。讲演会听众踊跃,如1924年有132次,讲演者432人,听众44050人;1925年讲演会315次,讲演者1165人,听众高达117880人。王诗琅译《台湾社会运动史》,稻乡出版社,台北,1988,第273页。
第五部分台湾文化协会(3)
复兴台湾地区的中华文化。针对日本殖民者企图移植日本文化并消弭中华文化的民族同化政策,文化协会开展了一场振兴台湾地区中华的浪潮,他们宣传台湾与大路同根同祖的历史渊源关系,进口大陆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介绍五四运动以来祖国的新文化新气象,强烈抗议殖民当局压制汉文的政策,要求恢复汉文在学校教育中的应有地位,同时编撰教科书、在社会上开办各类汉语学习班,这些举措得到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陈逢源指出:“中华民族自五千年来,虽有同化他民族的历史,但至今未被他民族所同化。这是中国历史上数见不鲜的事实。(日人)若要排斥中华的文化,人民必起而反抗。”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98页。
文化协会的广泛宣传带来了新文化和新思想,启迪了民智,推动了台湾民众祖国意识及民族意识的高涨,使之进一步认清了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文化灭绝实质,促进了中华文化在殖民地台湾的顽强扎根和传播,从而保持住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根基。所以,尽管在台湾民族运动中有所谓祖国派和自治派(台湾派)的区分,但二者在对待祖国和中华文化问题上的实质立场是一致的,日本人的内部资料《警察沿革志》就明确记载说:祖国派认为中国将来必能振兴并收复台湾,因此要传承自己的民族性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台湾派则认为,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中,苛政猛于虎,现时回归还不是时候。然而,日本人深刻的认识到,这部分人“也只是对支那的现状失望以至于怀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见支那隆盛,不难想象必回复如同前者的见解”。《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4页。
文化协会影响力的迅速提高及全台民众的广泛觉醒极大的刺激了日本殖民者,为了消弭文化协会掀起的民族运动浪潮,台湾总督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一,剥夺参与者的种种原有特权,如有公职者予以罢免,有专卖权者加以取消,等等;其二,利用御用士绅如辜显荣组织公益会和有力者大会等团体,公开与文化协会相对抗,并唆使流氓破坏文协的讲演会,比如1924年11月台北“陋风打破大讲演会”上的打斗事件即是;连温卿:《台湾政治运动史》,稻乡出版社,台北,1988,第78~79页。其三,直接运用警察镇压机器压制、取缔文化协会的活动,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治警事件”。但这一切似乎起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被罢免的公务员成了运动的斗士,被逮捕的文协会员声望反倒扩大了,对文协讲演会的横暴取缔激起了民众的反感和抗议,之后的参加者反而更多了。
文化协会发展的转折点乃出自内部的分裂。1920年代,正是中国、日本政治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日本共产党接着诞生,1923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随后北伐战争获得成功。所有这些都给了岛内外台湾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刺激,在大陆的台籍学生纷纷建立如平社、台湾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左倾色彩十分浓厚。在岛内,有连温卿等人组织的社会问题研究会,翁泽生、王万得等人组织的台北青年会,蔡孝乾等人组织的彰化无产青年派等等,一大批青年的思想急剧左倾。尤其是连温卿的社会问题研究会与山川均保持密切联系,“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理论及战术,以此对其领导下的青年加以宣传、煽动”。总督府称其“对于当时的民族主义统一运动战线,逐渐地酿成了无产阶级运动抬头的机运”。《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244页。这样在文化协会内部形成了连温卿等的无产阶级派、蒋渭水所率领的受中国革命影响较多的一势力及林献堂、蔡培火所代表的合法稳健派,三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明显起来。此一对立的根本即在于民族运动发展方针路线上的原则分歧。首先,文化协会从创办伊始,其政治上的最高诉求是设置有权处理台湾地方事务的台湾议会,实现台湾自治的目标,行为方式是温和的、非暴力的,主要手段是启发民智和请愿斗争,在体现坚韧毅力的同时又显现出隐忍等待的心态。林献堂自己就说过:“天助自助者,为贯彻目的,我们今后必须不屈服于任何障碍,纵使有时变成奴隶,也非隐忍不可。”《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208页。暴力和阶级斗争显然是与其不相容的。其次,文化协会是个由不同阶级、不同思想信仰的人们所组成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本身即存在着不同思想路线的斗争,《台湾民报》1927年新年号所载的蔡培火、蒋渭水、连温卿三人的文章正代表着文化协会内部三个不同派别的立场。蔡培火将文化运动局限于文化的范畴,蒋渭水谋求的是以农工为基础的全民运动的路线,连温卿则主张无产青年应占民族运动的主导地位。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若干问题的分析》,《台湾研究集刊》1993年第2期。随着加入文协无产青年的增加及旧文协会员思想左倾者激增,到了1926~1927年间,文协内部结构的天平已经开始倾向激进派的一边,要求改组文协的呼声高涨。连温卿甚至公开提出“如欲解放台湾人民,必须主张阶级斗争”。1926年10月,王万得等人面见林献堂,直截了当地申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为不可能实现的妄动,假使实现,也不能增进台湾人的幸福。这项运动是承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为之唱高调,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这种不彻底的妄动,宜予以中止。”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第269页。这就直接否定了林献堂等稳健派以设置台湾议会来达到台湾自治的斗争方略,二者的矛盾已不可调和。1927年1月3日的文化协会临时总会上,以连温卿为代表的左倾激进派掌握了领导权,林献堂等宣布退出,文化协会正式分裂。分裂后的新文化协会由于采行了激进的斗争方式加上殖民当局的全力取缔,在新竹讲演会事件和台南墓地事件的打击后,文协渐告覆没。
第五部分台湾民众党及台湾地方自治联盟(1)
文化协会分裂后,林献堂、蒋渭水等相继退出文化协会,并决意成立新的民族运动团体,继续遵循其合法、稳健,体制内斗争的道路推进民族运动的发展。1927年2月蒋渭水、蔡培火、林幼春等齐聚林献堂宅中,商议政治结社问题,蒋渭水提议成立主张“台湾自治”的台湾自治会,被总督府认定其“明显违反本岛统治的根本精神”,明令禁止。《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29页。5月又筹划组织台政革新会,揭示其纲领为“期待实现台湾人全体的政治、经济、社会解放”,殖民当局指其含有民族解放自决色彩,不予准许。6月正式决定成立台湾民众党,10月在台中举行发会式。
台湾民众党“以确立民本政治,建立合理的经济组织,及改除社会制度之缺陷为其纲领”,这项纲领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确立民本政治。这是针对总督专制统治及日本人对台湾政治资源的独占而提出的,其中心含义是要求还政于民,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在具体政策主张上,要求基层政权实施普选,拥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废除教育领域的日台人不平等并强烈要求“公学校教学应以日台语并用之”,“公学校应以汉文科为必修科目”。其二,建立合理的经济组织。台湾殖民地经济组织的特点是:日本人在各类经济组织如株式会社、水利组合中占据垄断地位,金融组织也控制在日本人(包括在台日本人和在日日本人)手中,由此引申出,日本人不但操纵着台湾工农业经济命脉,同时也透过资金优势掌握着台湾民族资本的发展前途,台湾人在经济上对日本资本的依附性正日益加深,民众党的经济政策就是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的,如“要求改革金融制度及紧急设立农工金融机关”,“改革专卖制度”等等。其三,改除社会制度之缺陷方面,民众党着重强调了两条:第一,“援助农民运动,劳动者运动及社会团体之发展”,第二,“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援助女权运动,反对人身买卖”。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国内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运动,应取阶级斗争,在帝国主义国内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应取民族运动——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这是世界解放运动的原则。”《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台湾民报》1927年5月1日。号召实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蒋渭水:《对台湾农民组合声明的声明》,《台湾民报》1927年6月12日。上述表明,尽管在文化协会分裂后民众党与新文协各行其道,但民众党仍然希望继续主导台湾的民族运动,并扩大对农工运动的支持,努力促成台湾全岛全民性的民族运动。
台湾民众党结党时曾宣布:“我党的目的只是为提高本岛住民的政治位置,安定其经济基础,改善其社会生活,如在纲领政策里所表示者。不但没有民族斗争的目的,更认为在此小地方如兄弟墙相争的情况并不能增进我们的幸福。”《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49页。强调“以合法的手段”进行抗争。但这一宣告并不能表明民众党就不是一个民族运动团体了。首先,民众党随后的各类决议和文章都不断强调了党的民族斗争目标。1928年7月民众党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宣言这样写道:“我们求台湾人之解放,对内先要唤起全台湾人之总动员,对外与世界上之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联系,共同奋斗,如此始能达其目的。”《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77页。1930年的第四次党员大会更申明当初之所以有不从事民族运动的申明,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客观情势之限制”而绝非本意。其次,民众党的一系列活动实际上就是台湾民族运动的发展和延续,譬如抨击总督专制统治和警察的横暴,发动向国际联盟控诉台湾“卑劣的”鸦片政策,揭露所谓总督府评议会花瓶摆设意义,要求废除封建保甲制,取消限制台湾与大陆间往来的渡华旅券制度,反对所谓始政纪念日,举办大规模的讲演会等等,无不包含着浓烈的民族斗争气息。再次,民众党也得到了台湾广大民众的支持,特别是以依靠人民大众进行民族运动思想为核心的蒋渭水一派在民众党内逐渐占据领导地位后,台湾民众对民众党的支持率大为提高。1927年,支持民众党的工人团体有20个,所属会员3188人,农民团体2个,所属会员362人,普通团体12个;1928年很快就上升为工人团体42个,会员12806人,农民团体4个,会员1022人,青年团体8个,会员409人,普通团体10个,会员866人。《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83~184页。
在192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民众党内以蒋渭水为首的一批骨干人物思想日趋激进。蒋渭水对社会主义观点并不排斥,相反,他还相当认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基本理念。早在1923年,蒋渭水即与连温卿、谢文达、石焕长、蔡式谷等人发起成立社会问题研究会,研究苏联革命及劳农问题。同年7月,又与王敏川、翁泽生等谋组台北青年会,其中的主要干部多倾向社会主义和民族自决主义。蒋渭水本人于1928年进一步发表了《台湾民众党特质》一文,强调:“台湾民众党有六个特质:民主的中央集权、解放团体、多阶级的党、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