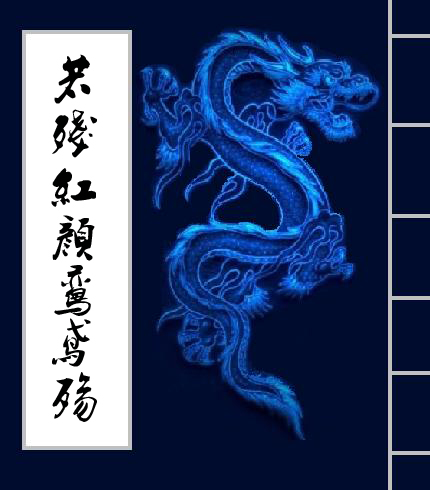花褪残红青杏小(完)-第9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没什么好听的,不会那么快长大。”我讨厌他靠近我。
“不,我要听一会儿。”他便趴上去听一阵儿,有时会咯咯地笑,我好奇他笑什么,却忍住了没问,管他笑什么!然后,他就把我拉到怀里抱着睡,而我的姿势永远只有一个——背对他,尽量蜷缩身子。
日复一日,时光像庭院里的风,倏地过去了。冬天来了,院子里常见的落叶也没了踪影,树上光秃秃的,偶尔有几只麻雀蹲在地上啁啾一下,便无了声息,四处有一种清冷的寂静。后来就下起了雪,或大或小的雪花飘落下来,檐下的冰棱长长的,风一吹,它们摇摇晃晃的,院子里便有碎冰落地的脆响声。
我守在屋子里无处可去,反正每间屋子都有暖盆,一向怕冷的我不必担心。到哪儿都有人跟着,我待在哪儿都无所谓。每天可以去花园,但身后的人寸步不离,有冰雪容易滑倒的地方是绝对不允许去的,而且待一会儿就得让我回来。次数多了,我也不用他们提醒了——套中人生活得久了,自然知道套子的边际在哪儿。我也不想让翠环她们为难,我相信孩子如果出了事,杨骋风真会让她们去死。哼,都是丫鬟,非要这么看紧我,我宁愿像翠环她们那样挨打挨骂,都不要睡在他身边!
就这么安静地过着日子,什么也不敢去想。杨骋风有时会拿些番商送来的新奇货品摆在我面前,我看都不看——二十一世纪的东西我都见过了,还稀罕这些?闲极无聊就看看上面的字,阿拉伯文最多,我都不认识,偶尔也会有英文字,上辈子学的差不多全忘了,连猜带蒙呗,闲着干什么?有时也曾动念头给孩子做点儿什么小东西,再一想算了,杨家有的是钱,早就准备好了,况且我什么也不会,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让杨骋风发觉我对这孩子有特别深的感情,虽然随着他在我肚子里一天比一天活跃,我确实已经很在意他了。
新年到了,我毫无感觉,也不敢有什么感觉。二十年来,没有一个新年比今年惨。我现在学会了麻木,不敢想,想起什么就会不断地流泪,想起什么都会让我失去活下去的勇气,想什么都不会比腹中这个一天比一天大的孩子带给我的感觉更强烈。不想,不敢想。杨骋风说我不会死,他说得对,我不会轻易死的,哪怕世界上只剩下最后一棵草,我也要舔着上面的露珠活到最后。我想活,无论什么情况我都要继续活下去。我逼着自己什么也不想。
我盼着他去湖州,甚至头一次主动和他说话——
“杨骋风,今天都腊月二十了,你不回湖州尽孝道?”
他不动声色,“咱今年不回去了,省得你动了胎气。”
“你自己回去吧,我不去,反正这里什么都有,翠环她们也都在。”
他笑了,“现在这么善解人意了,那么晚上……”
“杨骋风,你想都别想!”我扔了筷子。
“哈哈……司杏,什么时候你也开始玩心眼儿了?你只适合和天斗,不适合和人斗,以后别干这种事了。”我的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别生气了,只是开个小玩笑。”他收起笑脸,“我要和你在一起,实话说,我不放心你。”
我咬了咬嘴唇,我现在就像一个犯人,是杨骋风的生产机器,要给他生个儿子,儿子生出来,我的义务也该尽完了吧。这个孩子,会是个儿子吧?有时我也在心里祈祷:是个儿子吧,千万是儿子!杨骋风再碰我一下我都觉得难以忍受。
吃年夜饭时,杨骋风笑嘻嘻的,“司杏,来,这边坐,小心小心,肚里可是我杨家的小少爷小小姐,嘿嘿……”
我按捺着恶心坐了过去。
“来来来,吃菜,吃这个,这个补,吃了好。”他动手剥了只虾给我,掐头去尾抽出黑线,剥得一干二净地放在我面前,我不声不响地夹起来就吃,他歪着头瞧着,“你好像很喜欢吃虾。还记得那年过年你也吃了好些虾,到底是海边长大的。”
多少年前的事了,我早不记得了。
他吹了声口哨,“人说怀了孩子不能吃虾,腿多,生出来的孩子闹。我不怕,咱杨家的孩子就是得闹,闹了才有出息,那么木讷干吗。来,吃,使劲儿吃!”他笑嘻嘻地又剥了一只虾递给我。
唧唧歪歪的,有完没完!
“哈哈,明年就是咱三个人过年啦,不,五个,还有我爹我娘。”
什么咱们咱们的!我不做声地继续吃。
“司杏,一会儿晚上我们一起发纸?”他一边擦着手一边问。
“不。”
“发吧发吧,你总得下厨打个糕,做做样子就行。你也是主母了,这些事总得做做。”
我不吭声地吃完饭便回房了。
整座明州城都是爆竹声,我黑着灯坐在床上,看着那遥远的烟火——他们很远,离我很远。脑子空空的,一切都和我没了关系,我能活动的范围就是这么小小的一间院落,还有人跟在后面不停地说着,“少爷说……”这地方像坟墓,逼得我什么也不敢想。肚里的孩子动了,我轻轻地拍了拍他,“小家伙,闹腾什么,听见鞭炮声了?明年就该出来喽,出来和妈妈过年啊。”我的泪下来了,往后的日子便是这样的?
春天来了,我大腹便便的哪儿也去不了,天天只坐在窗前看柳眉儿泛黄,然后吐出小叶子,再长大长长,变成一树青翠。春天真是好时候,应该春衫单薄,应该心情爽朗,应该满怀希望,可惜我只能坐在屋子里,看着春天的变化。
杨家的花园也很有特点——富丽,大气。看得出来杨骋风并不是特别爱花之人,园里都是些名贵花卉,我叫不上名儿来,好看是好看,只是根本看不出主人的喜好。我猜想,若不是监视我,他一年也不会去园子里几次——标准的官家子弟啊,只是怎么就盯上我这丫鬟了?春天到了,含笑也该开花了,可杨家花园里没有,不知琅声苑的那株含笑如今怎样了——我一想到这儿,赶忙把心思转移,不敢再想下去。
我偶尔也会想到荸荠,便觉得心里很温暖,但是感觉很淡很淡了,仿佛他是多年前的醇酒,温暖而清淡。我想起他,就像想起了好朋友,让我牵挂。三次去到湖州的一切都封在我心里,谁也动不了,他离我远去了,是另外一个世界了。他们都在另外一个世界了,物是人非,我身陷在这座深院里,哪天真有幸逃脱,生命的轨迹也不会再和他们有什么交集了。
可惜明年花正好,知与谁同?更何况,今年花不好,明年的,更不敢想。
八个月了,我的身子愈发沉重,晚上睡觉觉得腰有点儿挺不住,和翠环要了枕头垫在腰后,不想杨骋风一上床就抽走了。
我忍着厌烦没有说话,他靠了过来,“是不是要些东西倚着?靠着我吧。”
我不理他,也不动。
“司杏,”他慢慢地说,“我知道你恨我,可都现在了,你就放一放吧。真的,我对你是真的,我敢把心挖出来给你看。别折腾自己了,我再不好也是孩子他爹,你就放过自己吧。”
我继续冷漠,放过自己?和绑架□自己的人在一起言笑调情,我还没修炼到那种程度。
我心如死灰地熬着,天天数着日子,终于熬到了生产。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生日又叫母难日了,确实是母亲受难的日子。那种生死之间挣扎的痛不是语言所能形容的。我生了一天一夜才把孩子生下来,当我听见孩子的哭声后,觉得整个人都空了。我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然后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得真沉,什么也没想,就是睡,像累了几个世纪,今天终于睡着了。
累,我累,我在梦里也是这种感觉。
累,我累……
作者有话要说:咳,比较沉重啊,说点轻松的事。
早上路过一个正在看报纸的人,扫了一眼大标题,某某队临阵换帅,某某火线赴职。某某队是我不熟悉的,估计是哪个球队换名来的,某某人却是我熟悉的。那是我青春时候知名度颇高的一名球员,足球队员。
现在足球都让人说烂了,媒体大众经常拿中国足球开玩笑。我看球的那时候还好,虽然已经走了下坡路,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烂事,但还可以看看。
那时候的足球远没有现在全民化,中央五也没有大规模的转播国外的联赛,也没像现在这样培养出一堆花痴女球迷(汗,别打我,窃以为,女球迷关注技战术的很少,大多是看哪个帅)。
那时候我们最喜欢的人是李承鹏和黄健翔——黄那时还不像现在这么不知天高地厚——最关注的报纸是《体坛周报》(为了看李承鹏的评论)和《足球》,后者前些日子看新闻说,已经停刊。国内足球的一切动向都牵扯着我们,网络根本不发达,我们学校算是条件尚可的,几乎每个教室都有电视,每逢有球赛,附近学校的男生会过来看球。
我总是坐在最后,一个人,谁也不陪,只为自己看球。后来据我当年的同学称,我挺有名,以至于对面学校的男生请我去当裁判。因为他们互相不信任对方提的裁判,看我经常在看球,便各派一名代表邀请我吹他们的决赛。
年少的时候真单纯,单纯又快乐。
如今,你问我,足球队中哪些人技术还不错?茫然,我连国家队里有谁都不知道,至于中超,自从改名我就没有看过。
年华似水。不经意,过去了。
第六十九章 受制(二)
一醒来就看见绿影子在眼前晃动,烦!“孩子呢?”我闭上眼睛问。
“你醒了,起来吃点儿东西?一天一夜,累坏了吧?还好,一切都好,我已经让人去湖州向我爹娘报喜了。娘子,大功臣呢!”笑嘻嘻的声音近了,我觉得眼前有点儿暗,知道他肯定低着头在看我。
听说一切都好,我放下心来。确实有点儿饿,我不情愿地睁开眼,果然见他有点儿黑眼圈的眼睛在盯着我,“这就起来?”我要动,他赶忙扶着我,一边唤着丫鬟上饭。
“这是什么?黑糊糊的。”我皱起眉头。
他一脸笑意,“穿山甲炖老母鸡,吃了补的,你先把汤喝了,润润身子。这穿山甲是只小个儿的,应该很嫩,我怕大的肉老你嚼不动。”
“儿子还是女儿?”
“儿子,八斤多。娘子,你真能生!”杨骋风的眼珠子随着我的手转动,“好不好吃?郎中说要补就不能多放盐,你凑合着点儿。”
“孩子呢,郎中有没有看过?”
“郎中看什么?又没病。声儿响着呢,蹬着腿哭,挺有劲儿的,攥着我的手指半天都扒不下来,小家伙!”杨骋风眉飞色舞地说着。
我的心放了下来,阿弥陀佛,不是畸形儿,希望也别有什么病,我急不可待地想看看他。
“快抱来给我看看。”
“在奶妈那儿,你先吃,一会儿送来。”
“奶妈?”
“对,我早让人找好了。”他倒掉我吐出来的骨头渣子。
“我自己喂,给奶妈做什么?”
“咱这种人家,哪有自己喂的!”
我放下勺子,“我自己的孩子我不喂,送给别人喂?”
“好好好,你有功你最大!”杨骋风让了步,“不过,”他迅速往我胸前瞟了一眼,凑上来小声说,“你有奶吗?”我的脸红了,我哪知道有没有。有吧,我觉得胸有些胀。
孩子抱来了,我迫不及待地接过去,小家伙的皮肤还有些褶皱,白胖胖的,闭着眼睛正在酣睡,我不自觉地微微笑了。
“有点儿丑。不过听说新儿丑七天,过些日子就好了。”杨骋风也看着孩子。
丑不丑,他也是我的儿子。我看着他,心里生出一种特殊的情感——这是我儿子?我在这一世,做了母亲?
“司杏,咱们有儿子了!”杨骋风盯着小东西小声说。
我不理他,只盯着孩子看,又把他放下来,解开包袱,禁不住笑了,小胳膊小腿儿小手小脚,怎么长成大人啊!
我捏着他的小手,真软,我笑了。
“幸福吧?我也觉得很幸福。”杨骋风捏着孩子的另外一只手,“咱们一家三口,多幸福!”
我正要刺他两句,小家伙也似要表达意见,哇地哭了,接着,一道小水柱蹿了出来,尿了!
我手忙脚乱地按住包袱想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