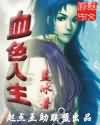笑面人生-第20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情形了。想到这些,完完全全能看到明天的我们实在不该有什么迷茫,有什么怅惘
而在那里徬徨,这点道理实在是再简单不过了。在这个世界上,看不见远方的人是
盲者。光盯着远方的人也走不好眼前的路。想对这个社会作点什么,总要付出牺牲。
与伙伴们牺牲和那些献出生命的勇士比,我们能作出的那点儿,应该说不能同日而
语。就冲这一点,我们不该踏踏实实、心安理得地干好我们自己眼前的事吗?
最后,我想用一位作家的散文诗来结束我的小文,并且把它当作我送给与我一
样的伙伴们一件小小的札物。
“夜,不全都是黑的。
白天,也未必全都光明。
即使是风雨交加的夜晚,
透过重重黑幕裹着的天庭——另一隅,
依然闪耀着希望的星群。
希望也不仅仅只是光明——生命的价值,
始于分娩的痛苦;
今天,始于划破昨夜的黑暗。
是的,夜不全然是黑的!
不懂得这一点,社会在风和日丽的今天,
只见煌煌’光明下的另一面——物体的阴影’”
二汽的伙伴们,
祝你们成功!
文章登出后,伙伴们反映强烈。我想,我的热情和实在感染了他们。所以我说,
第一点就是尊重伙伴,切莫教训人。
第二点是实事求是,切莫牵强。相声言语犀利,锋芒外露,这样有人对社会上
看不惯的现象,真想用相声一刺而后快。青年人买维纳斯,老年人找到我们:“你
们好好写一段相声,我们中国人家里摆光身子的小人儿,成何体统?”社会上流行
穿喇叭裤,看不惯的伙伴就出主意:“你们一骂喇叭裤,穿得准少,纯粹臭阿飞!”
我们只能在理解他们情感的基础上告诉他们:“我们不能那样去写,那样去演。”
社会上流行过这样一个故事:某个单位下了行政命令:青年工人的裤腿不许小于六
寸五。于是在这个工厂的门口,青年们刷了一张“广告”。“广告”内容如下:本
厂青年徒工为响应领导抵制瘦裤腿的裤子之号召,恃成立业余民族服装店。承做中
国传统之挽裆裤,男女适宜,前后不分,穿着方便,黑白分明,穿着时不用裤带,
只需将小腹收后,屏住气息,左右一挽,往里一掖,放开肚子即可……。毋容置疑,
这张“广告”是不适当的行政命令招来的。相声中的道理,要人信服,谈出的话让
伙伴点头才行。实事求是,坚持两分法、防止片面性,应该说是必须注意的很重要
的一个方面。我们在相声《谈美》中,设计了父亲和儿子因为摆维纳斯像的一场争
论,从父亲之口,讲出了我们认为较为正确的看法:“这东西是个好东西,分摆在
什么地方合适,摆你们家,你是当演员的,这个塑像和你那套家具也衬。我有我的
乐儿,我就希望我这桌子上摆个宜兴的泥茶壶,墙上贴两副对子,挂幅国画,别人
看着舒服,我瞧着也不咯愣。”通情达理的话语,赢得人们的赞同。牵强的解释,
呆板的指责,不会取得预期的艺术效果。
第三是开掘知识,切莫空洞。伙伴们经常讲:“我们不爱听领导讲话。
嗯、啊、这个、那个,说了半天不知说什么。”语言的空洞是引起不感兴趣的
原因之一,但就是讲了知识,不往深处开掘,也同样引不起人们的兴趣,所谓开掘
就是跳出一般。
林业部的副部长董智勇同志,刚刚从朝鲜考察林业回国,当天下午就叫我去他
那里。他问我:“小姜,你说树木、森林的用途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盖房子,做家具。”他笑了,接着问:“光砍下来才有用?”我慌忙说:“不,
树木有光合作用,为人类提供氧气,树根能蓄水,是个小水库,还有……”我搜肠
刮肚地也没有再找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许多知识就是这样,当你认真地去想时,才
发现自己认为了解的却是很肤浅的一点点。
这天下午,副部长找来宣传干部和我一起座谈,他们讲的那些材料使我瞪圆了
眼睛,记了那么满满的一本。我几乎在知识的海洋里重新认识了树木、森林,认识
到它不仅有着物理价值,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价值,心理上的价值,简直无法用金钱
来计算。两个月后,我和李文华同志创作出《严重警告》。
董副部长听后对我们说:“你们这相声,比我作10 个报告还有用。过去小青
年们一听人讲林业就头痛,可听你们讲林业的事,他们从笑声中受到了教育。”我
们在首都体育馆演完了相声《谈美》,和作家刘厚明同志同车。他对我们说:“我
刚才听我身后的服务员谈话:‘对,不和谐就美不起来。’当然,自然界中也有现
代派的不和谐的美。但是,从普及意义上讲,你们一刻多钟的相声,让人明白了这
样浅显的美学知识——和谐产生了美,你们这个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是的,我
们也不多要求,一个段子给伙伴们一点收益,积少就能成多。有人讲要给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大厦添砖加瓦。李文华同志讲:“咱们给基础上的土踩几脚,让它磁实点
就行。”知识、道德、情操,正是做人的基础。我们自己受到了教育,再把感受告
诉给伙伴,一点点把思想基础打得结结实实,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前进,一起有胜
利的喜悦,一起有生活的快乐。这是件多值得痛痛快快笑上一场的事啊!
八
相声越演越多,作品可越来越少,观众要求越来越高,品味也越来越高。
渐渐地,我感到我们自己的危机越来越严重。
我在《北京晚报》写了一篇《忧与虑》的短文:
忧与虑
我写相声,也演相声。听到观众们讲“我最喜欢听相声”,倒产生不少的忧虑。
不是忧观众,而是忧自己。
过去创作一段相声,深入生活,搜集素材,构思命笔,排练演出,反复修改,
最后录音录像。《如此照相》写了半年,《诗歌与爱情》写了八个月。
现在创作一段相声,下面前迎后送,演出接连不断,领导登门看望,随即录音
录像,演员自己台词还不“拱嘴”,街头孩童们把主要段落已经背得很熟了。有人
问:《我与乘客》、《谚语谈》的录音怎么还吃“桑子”——台词打了“喀奔儿”,
我只好苦笑了之。因为谁也不会相信,我们的录音录像距离背台词不过几天!听到
了意见想改,生来早作成夹生饭了,难怪人家吃了皱眉头。
可就是这样的情况,演出倒一天比一天多,一年中居然分不出“热季”、“淡
季”了。
谈忧又提以上这些,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担心自己能不能适应人们对相声热切
要求的形势。
听到了一些议论,也忧。这个演员‘不火了”,观众反映不热烈;那个演员
“庸俗了”。乍一想,真感到相声有点“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细一琢
磨,忙来忙去,是好事。不如此思索,艺术怎么向前发展呢?问题无非是由观众热
烈的期望和不满足的批评所产生的。那么在如坐针毡的状态中冥思苦想一番,无外
乎仔细的思考,虑出一点毛病生成的原因,虑出一点前进的道道来。
观众热切地期望着相声的数量,但并没有忽视它的质量。而且他们最公正、最
无私,好就鼓掌就笑,不好就沉默就失望,再遇到不好的,先是笑,笑完再撇嘴。
评论也“尖刻”了,就是对待一些传统的表演手法的出现,觉着不合时宜了。
观众不讲演出的新与旧,而是说:“俗气,格调不高!”看看,不是新与旧了,是
是与非了。
再有就是观众的主要成分青年的特点——真敏感。有的包袱,你没铺垫,他就
明白了,这当然谈不上包袱“响”了。再想想现代青年的生活内容面之广,这些都
应该好好地虑一虑了!
思来索去,人们的要求高了,连时代的节奏都变了。
于是,为了保证剧场效果,不注意“包袱”质量的表演出现了,不根据内容的
需要而只追求形式上的“新异”出现了。吉他伴奏,通篇的口技挤进相声的表演中,
这一切,又困扰着我……
鲁迅先生曾断言,就是在中国的这些口头文学中,以后要出现福楼拜、托尔斯
泰。天呵,我初中毕业,李文华小学二年,加起来寸高中肄业。
我们如果有志向这个方向走,当付出怎样的努力呀!……
今年年初去长春,飞机在沈阳耽误了几小时。再起飞时,天空黑洞洞地像块大
幕布。忽然,从机窗向下望去,下面灯光闪烁,有人告诉我,那是四平市。我只见
那昏暗的灯光,一闪闪地好像在向我们机上的人们炫耀着什么,别的什么也看不见。
这时,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底下诺大的城市中,最有实际内容的是那样默默地
不为人们所见而蕴含着;而点点灯火,充其量不过是个灯泡而已。于是,一点想法
从心底油然升起:如果说,我们在台上的一段相声,就是那点点灯火,那么我们应
该在无声的时候,用全部的青春和热血,去做更有实际内容的工作……
写于1985 年底
改于1996 年8 月
《大能人》折摄记
看了我和李文华演的电视小品《大能人》,我“噗哧”笑了——为自己过火的
表演笑了。真是干什么都不容易呀!没出所料:演“砸”了。但我并不后悔,不信,
有拍摄五篇日记为证。
2 目26 日
爱人替我传呼电话:北京电视台导演林汝为下午来找。见了面,原来是叫我和
文华一起演个电视小品。“剧本呢?”我问。林递过一张《人民日报》,上面有一
篇小说《大能人趣话》。我把报纸递给她:“这是小说呀!”“只要你们同意合作,
马上搞,争取两个星期完成!”天呵!两个星期,大小这也是个剧呀!除了我们有
赴港演出的准备工作不说,就是排戏的话,光写剧本,分镜头,选景地,找演员,
那也是一大摊子的事呀!林导这个人很固执,过去我和她合作过,她是个想干非干
不可的人,我知道她该讲理由了:“这是个农村题材,讲尊重妇女,提倡精神文明
的事,主题不错,3 月份是文明礼貌月,你们二位该作点贡献才对呀!”(看看,
将上军了)不容分说,她走了,说是找我们领导去,真没办法。剧本的任务她交给
我了。真是大松心,您知道我会写吗?有了,找八一厂编剧李平分,他笔头子快,
看在多年朋友的面子上,让他在我这儿开开夜车。
一个电话,平分风尘仆仆地来了,我一提他就叫起来:“我的天啊,一个剧要
在一昼夜搞出来,要命哪!!”甭管他嗓门儿多大,我是不让他走了。
吃完饭就念小说,他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短篇:“不错,语言真好,就怕到剧
里没味了!”我说:“甭管味儿,先搞出来再说”,我俩冲着录音机拉架子,一直
说到我睁不开眼为止。我睡了,他还在写。我知道第二天我醒了以后,他准睡着了,
但剧本也准能出来。我了解他。
3 月1 日
真没想到领导看了本子,同意了。前天的会在我们家开成了。他们这个小班子
搭得真不错,怎么找的,全是喀崩脆的急脾气。制片主任梁士龙说:
“没问题,玩命干!”摄影师唐果说:“我趴着拍,也要拍下来!”和林导合
作的鲁导更是急,他开会都坐不住。尽管走路的姿势不好看,可他总爱在屋里踱来
踱去。看来走路增加了他的思维,他把每一个细节想得都很细致。
我想插嘴,他说:“别的你甭管,你能把‘大能人’演好就行了!”早上林导
给我打电话:“今天我开夜车分镜头。”我问她:“就一个本子,你拿什么分?”
“你和平分听录音!”真有她的。
下午,剧务小冯打电话告诉我:“鲁导已经到郊区选景去了,梁士龙去找演员。
美工们拿着那张报纸在准备服装,5 日试装,6 日读剧本,7 日集中进景地,8 日
开拍,14 日完成!”天呵,够赶啰啊!
3 目8 日
连搞过电影的平分都惊讶:“太快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也是个摄制组呀!”
我想原因很简单:人心齐!一班子人,一呼百应。
昨天上午集中,两辆汽车解决问题,连人带机器全送到了西山脚下的海军招待
所。吃过午饭后,全体进入拍摄现场——四季青人民公社。看完两个景地就晚上6
点了。回来后导演说戏,演员对词儿,一直到11 点。我和文华老师回到屋,他问
我:“鲁导他们说画角度,这是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睡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