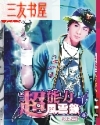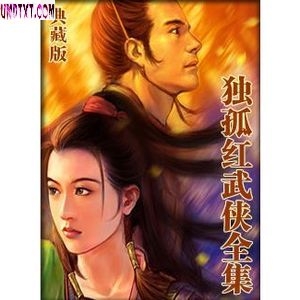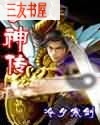随想录-第2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杂志上用“马琴”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篇《广州》,是杂志社约我写的地方印象记。文中提到那座可以拆开的海珠桥,我写道,听说这是从瑞士买来的旧桥。一位广东朋友对我这样讲过,我不加考虑,就把他的话抄录在文章里。这句毫无根据的话让当时的广州市政府的人看到了,他们拿出可靠的材料,找发行《中学生》杂志的开明书店交涉,书店无话可说,只好登报道歉,广告费就花去两百多元。我贩卖假话闯祸的事大概就只有这一件。但我写文章时并不知道这是朋友的信口“随说”。像这样的事以后还有,只是没有闯祸罢了。因此我应当补充一句:坚持不说假话,也很困难。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欺骗读者。我倒愿意拿本来的面目同读者见面,我说把心交给读者,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不是以文学成家的人,因此我不妨狂妄地说,我不追求技巧。如果说我在生活中的探索之外,在写作中也有所探索的话,那么几十年来我所有追求的也就是:更明白地、更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旧社会中写作,为了对付审查老爷,我常常挖空心思,转弯抹角,避开老爷们的注意,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决不是追求技巧。有人得意地夸耀技巧,他们可能是幸运者。我承认别人的才华,我自己缺少这颗光芒四射的宝石,但是我并不佩服、羡慕人们所谓的“技巧”。当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笔抹杀,因为我没有权利干涉别人把自己装饰得更漂亮。每个人都有权随意化妆。但是对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红的这样一种文章我却十分讨厌。即使它们用技巧“武装到牙齿”,它们也不过是文章骗子或者骗子文章。这种文章我看得太多了!
三十年代我在北平和一个写文章的朋友谈起文学技巧的问题,我们之间有过小小的争论,他说文学作品或者文章能够流传下去主要是靠技巧,谁会关心几百年前人们的生活!我则认为读者关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我说,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什么是技巧?我想起一句俗话:“熟能生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经验。写熟了就有办法掩盖、弥补自己的缺点,突出自己的长处。我那位朋友写文章遣词造句,很有特色,的确是好文章!可是他后来一心一意在文字上下功夫,离开生活去追求技巧,终于钻进牛角尖出不来。当然他不会赞同我的意见,我甚至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我还说,生得很美的人并不需要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生得奇丑的人,不打扮,看起来倒顺眼些。我不能说服他,他也不能说服我,我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探索的路。
探索之三(2)
四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两个都还活着,他放弃了文学技巧,改了行,可是取得了新的成绩。我的收获却不大,因为我有一个时期停止了探索,让时光白白地飞逝,我想抓这个抓那个,却什么也不曾抓住。今天坐在书桌前算了算账,除了惭愧外再也讲不出什么。失去了的时间是找不回来的。但是未来还不曾从我的手中飞走,我要抓紧它,我要好好地利用它。我要继续进行我生活中的探索,一直到搁笔的时候。
我不能说我的探索是正确的,不!但它是认真的。一九四五年我借一个小说人物的口说明我探索的目标:“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那么我已经做到了?没有,远远没有!所以我今天仍然要说: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也不想做一个艺术家,我只要做一个“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的人。为了这个,我决不放下我的笔。
二月二十八日
探索之四
人各有志。即使大家都在探索,目标也不尽相同。你想炫耀技巧,我要打动人心,我看不妨来一个竞赛,读者们会出来充当义务评判员。
我在这里不提长官,并非不尊敬长官,只是文学作品的对象是读者。例如我的作品就不是写给长官看的,长官比我懂得多。当然长官也可以作为读者,也有权发表意见,但作者有权采纳或者不采纳,因为读者很多,长官不过其中之一。而作者根据“文责自负”的原则对他的作品负全部责任,他无法把责任推到长官的身上。任何人写文章总是讲他自己的话,阐述他自己的意见,人不是学舌的鹦鹉,也不是录音磁带。
前些时候人们常常谈起“长官意志”,我在去年发表的《随想录》中也讲了我对“长官意志”的看法。我认为长官当然有长官的意志。长官的意志也可能常常是正确的。长官也做报告,发表文章。这些报告和文章中所表达的就是长官的意志,而且它们大都是人们学习的材料。我没有理由盲目反对任何长官的意志,可是我无法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哪怕是长官的意志。我有过一些奇怪的经历。五十年代有一份杂志的编辑来向我组稿,要我写一篇报道一位劳动模范的文章,人是编辑同志指定的,是一位技术员,编辑同志给了我一些材料,又陪我去采访他一次。我写好文章,自己看看,平平常常,毫无可取之处,但是到期又不能不把稿子送出去。结果文章不曾在杂志上刊出,编辑同志不好意思退稿,就把文章转给一份日报发表了。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编辑的“意志”并不错,错在我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当时我也为这种事情感到苦恼,但是我总摆脱不了它。为什么呢?大概是编辑同志们的组稿技巧常常征服了我吧。这位去了那位来,仿佛组稿的人都是雄辩家,而且都是为一个伟大目标服务的。我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也可能是我的思想不解放。我总以为过去所作所为全是个人奋斗、为自己,现在能照刊物的需要办事,就是开始为人民服务。这种想法,我今天觉得很古怪,可是当时我的确这样想、这样做,在“文革”的头三年中我甚至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传达室工作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因此我只好经常暗中背诵但丁的诗篇,想象自己就站在阿刻龙特(Acheronte)河岸上,等着白头发的卡隆(Caron)把我当做“邪恶的鬼魂”渡过去。① 真是一场但丁式的噩梦啊!
现在大梦已醒,我不再想望在传达室里度过幸福的晚年了。我还是要写作,而且要更勤奋地写作。不用说,我要讲我自己心里的话,表达我自己的意志。有人劝我下笔时小心谨慎,头伸得长些,耳朵放得尖些,多听听行情,多看看风向,说是这样可以少惹是非,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九十。好意可感,让我来试一下,也算是一种探索吧。但这是为聪明人安排的路。我这个无才、无能的人能走吗?
二月二十九日
友谊
《随想》第四十在《大公报》发表后,我就放下笔访问日本。我在日本朋友中间生活了十六天,日子过得愉快,也过得有意义;看得多,也学到不少;同朋友们谈得多,也谈得融洽。人们说“友情浓于酒”,我这次才明白它的意义,我缺乏海量,因此我经常陶醉,重要的感觉就是心里暖和,心情舒畅。我忘不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我到东京后不久,日本电视台安排小说家水上勉先生同我在新大谷饭店的花园里对谈。对谈从上午九点开始。那是一个很好的晴天,但忽然刮起了风。我们坐在园子里晒太阳,起初相当舒适,后来风大了,负责接待我们的清水正夫先生几次到园子里来,可是他只能站在线外,因为我们正在谈话,录像的工作正在进行。他几次仰头看看风向,匆匆地走了,过一会又跑回来望望我,伸起手辨辨风向,似乎急得没有办法。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可是我不能对他讲话,我的膝上盖着大衣,还是他先前给我送来的,我没有把大衣穿在身上,只是因为我不愿意打断我们的对谈,即使风吹过来我感到凉意,却也可以对付过去。这一个上午的对谈并不曾使我受凉,见到清水先生我还笑他像一位善于呼风唤雨的法师,后来听说他当天晚上在事务局(接待办公室)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是既然有风就不该安排在园子里举行对谈。我二十五年前就认识清水先生,当时他带着松山芭蕾舞团第一次访华,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舞剧《白毛女》,以后在东京和上海我都见过他,可是少有交谈的机会。他是有名的建筑师,又是松山芭蕾舞团的团长,这一次他领导事务局的工作,成天陪同我们活动,就同我相熟了。他和其他在事务局工作的朋友一样,从清早忙到深夜,任劳任怨。他究竟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
我再说第二件事:主人作了安排,要我在东京朝日讲堂里宣读一篇讲稿,题目是《文学生活五十年》,规定的时间是四十分钟。我在上海家中写好一篇七千字的讲稿,在北京请人译成日文,一起带到东京。讲演会在四月四日举行,前一天晚上,事务局的朋友建议请作家丰田正子女士在会上念译文。丰田女士是亡友江马修的夫人,也在事务局工作,她一口答应下来。为了念得流畅,取得更好的效果,她熬了一个通宵把译文重新抄写一遍。她又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友谊!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我也不想在这里列举了。在一次招待会上我讲过这样的话:“当中国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保持沉默的时候,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和开高健先生却先后站出来为他们的中国朋友鸣冤叫屈,用淡淡的几笔勾画出一个正直善良的作家的形象,替老舍先生恢复了名誉。……我从日本作家那里学到了交朋友,爱护朋友的道理。”这决不是说过就忘记的“外交辞令”,我讲的是简单的事实。他们都是为了什么呢?
每天我睡得晚,想得多,我需要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我对朋友们讲真话,讲心里的话。我虽然是一个感情不外露的东方人,可是谁触动了我最深的感情,我就掏出自己的心交给他。究竟为了什么?我一直在想。我想得多,但不是想得苦。我越想越是感到心里充实,越想越是觉得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掏出了自己的心,我并不感到空虚,因为我换来了朋友的心。我感到我有两倍的勇气,有两倍的力量。究竟由于什么?我得到回答了:由于友谊。
在日本访问的十六天中我流过两次眼泪,第一次是在羽田机场,我们离开东京去广岛,同朋友们握手告别,一位在事务局工作的年轻姑娘忽然哭出一声,泪珠滚滚地落下,这个时候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另一次在长崎机场,我们结束了访问从那里动身回国,西园寺公一先生从横滨赶来送行,他的腿关节有毛病,拄着手杖陪我们到机场,我走出候机室的时候,最后一次向着站在平台上的朋友们挥手,忽然看见了西园寺先生、清水先生和其他几位朋友的眼泪,我真想转过身跑回去拥抱他们。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却无声地哭了。我含着泪水上了飞机。我感谢这样的眼泪,它们像春天的雨灌溉了我干枯的心灵,培养了友谊,培养了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从长崎到上海只需要一个半小时,访问结束了,但是友谊将继续发展,流传到子孙万代,即使我的生命很快化为尘土,我那颗火热的心仍然在朋友们中间燃烧。我们的友谊决不会有结束的时候。
四月二十四日
春蚕
我在中国“文坛”上混了五十几年,看样子今后还要混下去,一直到我向人世举行“告别宴会”为止。我在三十年代就一再声明我只是一名“客串”,准备随时搁笔,可是我言行不能一致,始终捏住我那枝秃笔不放,无怪乎后来激起了“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公愤”,他们将我“打翻在地,踏上一脚”,要叫我“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确把我赶出了文坛。我自己没有办到的事他们办到了,这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吧。但可惜不多久“四人帮”及其爪牙们忽然无踪无影,我说不出他们躲到哪里去了,不过我知道有不少的人真想一口一口地咬他们身上的肉。
由于读者们的宽大,我又回到了文坛。我拿起了被夺去十年的笔,而且参加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阔别十七载的友好邻邦。对日本朋友、对日本读者我也说我不是文学家,我缺乏文学修养,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我把心掏出来交给朋友,交给读者。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不是文学家,所以我不用管文学上的什么清规戒律。只要读者接受,我的作品就能活下去。文学事业是人民的事业,而且是世界人民的事业,这个事业中也有我的一份。除非我永远闭上眼睛,任何人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