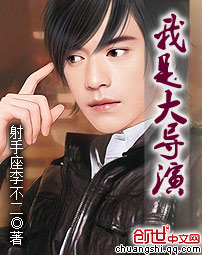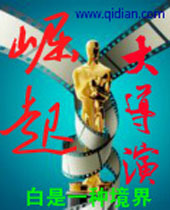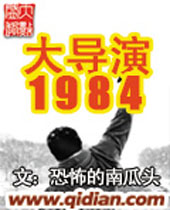大导演李翰祥 作者:窦应泰-第6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的,有的。”项囗见李翰祥如此关切,就信口为他诵读阳翰老为他所作的七律一首:
烟雨楼头思往事,
康乾两代展雄图。
咸丰碌碌慈禧贼,
窃国谋权亦可诛。
李翰祥来到第三化妆室。香港演员梁家辉正在镜前接受化妆师的精心化妆。梁家辉的身旁,围坐着两位电影杂志的记者。梁家辉在化妆的间歇,回答着女记者对他的提问。
梁家辉:“我是个影圈新人。很庆幸随李翰祥先生来内地参加拍摄《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的工作,况且是饰演一代君主。我带着对北京、对清宫的各种猜想来到北京,来到真的故宫,真的热河行宫,真的颐和园中,体味着封建帝王的生活。一切都是真的,实实在在,唯独我这个皇帝是个假的,想来可也挺滑稽。”
记者:“听说李导演当初之所以选中你来饰演咸丰皇帝,是因为你非常像意大利画家郎士宁笔下的奕囗的画像。同时也听说你在来内地拍片时遇到了许多麻烦,是吗?”
梁家辉:“在香港应该说拍电影的机会是有的。但是像这种如此辉煌壮观的场面,严谨的剧本结构,以及强手云集的大型历史影片,恐怕在海内外电影史册上也是不多见的。所以说,有机会参与并作为主演,也是很光荣的。当然,我在拍片的当中有很多的困难,主要演员几乎全是内地的,只有我一人来自香港,所以在语言上就是最大的难关。在拍戏的时候大家讲普通话,唯独我自己讲粤语。大臣和贵妃们谁也听不懂,有时逗得他们捧腹大笑,笑得我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了。后来,我就下决心来学习普通话,利用拍片的间歇来刻苦学习普通话。由于有大家的帮助,才使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基本上学说了普通话。我非常敬佩和感谢项老,他是一位内地的老演员,他没有因为我是‘香港来的新仔’而有所轻视。他十分耐心地教我念对白,后来,我才逐步地达到了李翰祥先生所要求的念白水平!……”
北影的仿古街道上,已经是人头攒动了。一轮火红的旭日冉冉地升起来,它照亮了那条被美工师临时装饰起来的菜市口大街。所有的店铺招牌在眨眼转瞬之间,变成了菜市口附近街道的景色。近干名群众演员均已化妆完毕,男女老幼,熙熙攘攘。晚清时处决重要人犯的紧张气氛渐渐形成了。
导演李翰祥和两位摄影师出现在一架能够上下移动的巨大拍片斗车上。面对着脚下那黑鸦鸦的人头,李翰祥将第五十七场分镜头剧本的内容,用最简洁的语言交代给两位摄影师。
第五十七场 菜市口 口外
(特)“菜市口大街”街牌。
(全)街道、房上,站满观斩的人群,水泄不通。(画外)
“别挤了,让开!”
清兵推赶人群:“让开……”
(近)一张布告(拉)看布告的人群被一群清兵推至墙边。
(全)人群中分开一条路。肃顺关在囚车中押来,人群激
愤。房上的人向肃顺掷脏物。
(特)“别部正堂”、“大理寺”牌子(移)监斩官行入棚内。
(全)囚车在人群中经过。
(近)肃顺头上、脸上落满蛋黄、果皮……
“预备——”李翰祥站在高高的吊车上,远远地望见肃顺的木笼囚车从仿古街的一端出现了。人群立刻向囚车拥来,李翰祥不失时机地将手一挥,叫道:“开拍——!”
北京初夏的傍晚。暮色沉沉。
一辆大型银灰色工作车疾驰在北京通往京郊圆明园外景地的公路上。将去那里拍摄《火烧圆明园》最后一场重点戏——火烧圆明园的香港导演李翰祥,坐在他的那间剪接室里,正在与一位记者闲聊。当那位年轻的记者向李翰祥询问在拍摄完《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两片后,是否有外界所传的那样——拍摄电影《徐悲鸿传》的计划时,李翰祥兴致勃勃,在越来越凉爽的晚风吹拂下,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李翰祥说:“说到为什么想拍《徐悲鸿传》,那要追溯到1978年。那是我第一次回内地,不是为了拍戏,而是到故乡看看。那时恰巧我导演的《倾国倾城》在北京内部放映,一些过去在北京国立艺专的老同学对这部影片很感兴趣。大家一起回忆当年的学校生活,回忆起难以忘怀的徐悲鸿校长。同学们对我说,你是拍电影的,你最好能把咱们老校长的一生拍出来。对于徐校长我是非常景仰的,能把这位艺术家、教育家的一生般上银幕,作为学生的我当然非常高兴了。我马上找到徐夫人——廖静文先生。那时她的回忆录《徐悲鸿一生》还没有写出来。听说我想拍《徐悲鸿传》,她非常高兴,因为她知道我熟悉徐悲鸿,有条件把这部影片拍好,最后便同意由我来拍。之后,几位熟悉的朋友找到了我,要求给我写剧本,我很高兴。几个月后,他们把写好的剧本寄来了,一看名字我就奇怪了,为什么不叫《徐悲鸿传》?难道徐悲鸿的名字没有号召力?再一看内容,我认为,他们塑造的徐悲鸿和我所知道的徐悲鸿不一样,他们将剧本搞成了徐悲鸿早年的恋爱故事,并没有把这样一位大画家、大教育家,在艺术上的成就、对绘画理论的发展以及他怎样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奋砥砺的成长过程表现出来。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就把《徐悲鸿传》先放了下来。后来根据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的建议,我开始着手拍《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
晚风习习吹来。在闷热如火的白天,李翰祥在这辆巨大的工作车里,在高温中将最近一批样片进行了剪接。现在,他觉得忙了一年多的《火》、《垂》两片已经接近了拍摄的尾声,接下来的便是繁忙紧张的后期制作。今夜,李翰祥将亲赴京郊圆明园外景地,他将在那里执导一场最精采的节目!他将在那里放上一把冲天的大火,亲手将那偌大一座耗资六十四万人民币制成的圆明园拍摄实景,化成一片废墟。所以,当他的最后杰作即将完成的时候,李翰祥的心情既紧张又轻松。此刻,他坐在向外景地飞驰的灰色工作车里,向赶来采访火烧圆明园夜景的记者,坦率地纵谈未来的拍摄计划。
李翰祥继续谈道:“在《垂帘听政》的拍摄过程中,有一天我接到廖静文先生打来的电话,说她写的那本关于徐悲鸿的书已写好了,其中有一段还写到我。不久我就收到了这本赠书。当时因为忙,我只翻了翻,便搁下了。后来从东陵拍戏回来,听组里人讲《徐悲鸿一生》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在旅途中他们手不释卷看得那样津津有味,促使我连夜看了这本书。书中写了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教育家艰苦奋斗的一生,包括很多名画的创作过程,也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书中也写了爱情,写了徐先生的理想和他的日常生活。我感到这是我了解的徐悲鸿。我马上找了廖静文,告诉她我拍完《垂帘听政》,将立即动手写剧本。这是我的一个新计划,我希望将来能变成现实……”
工作车在京郊那偌大一片仿古的建筑前缓缓地煞住了。言犹未尽的李翰祥从工作车上走下来,在苍茫如血的暮霭之中,李翰祥望见雄浑壮丽的“大水法”前,十只铜狗正在奋力地喷吐着雪白的水花。在一盏盏水银灯的映射之下,水柱闪射着绚烂的异彩。一大批充当英国侵略军的战士们,早已经化好了妆。工作人员正紧张地忙碌着,做着纵火的准备。为了防止在焚火时火势蔓延,几辆消防车停在外景地附近。摄影机在不同的角度均已架好。在渐渐昏黯下来的天空下,圆明园场地人头攒动,喧声嘈杂。
“翰祥兄,这么大的一堂布景放火将它烧掉,实在是有些可惜呀!”制片主任陪同着几位从香港来观看李翰祥拍摄最后大场面的影界友人,在暮色下沿着一条小路走过来。李翰祥看见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与他友谊深厚的拜弟胡金铨。现在的胡金铨早已是香港影坛上最有影响的导演之一。他所执导的《大醉侠》、《大地儿女》、《龙门客栈》、《侠女》等影片,不断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其中胡金铨所拍的《侠女》1975年曾获戛纳影展的综合大奖,胡金铨同时又成为首获导演奖殊荣的华裔第一人。1978年胡金铨又成为英国《国际电影年鉴》上所列的世界五大导演之一。此次胡金铨来北京,就是来观赏他引为师长的李翰祥所执导的历史大片《火烧圆明园》中最精采的“火烧”场面的。所以,胡金铨等影界友人已经提前一步来到了圆明园外景地。
“是的,金铨,我好不容易将圆明园这堂外景在京郊搭起来,可谓耗资巨大,煞费苦心啊!”李翰祥将其他港客请让到他的工作车里歇息,自己却独自与胡金铨相偕而行。他们两人沿着“大水法”通往“远瀛观”方向的小路上走来,两旁均是些奔忙的人影。李翰祥将无限留恋的眼光投向那些由木料、硬塑料、石膏等原料,精心接雕的廊柱、拱门,对胡金铨说:“尽管我也对这些仿古的建筑十分留恋,焚烧掉确实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可是,我李翰祥是为了让未来的影片增加真实性,才不得不忍痛割爱的!如果我对这些仿古建筑不采取真烧真毁,只是象征性地用火烧掉一些模型的话,那便失去了拍摄《火烧圆明园》的真正含意!烧掉六十四万人民币虽然是一种损失,但是大量的拷贝卖出去以后是可以将损失成倍地收回来的。更主要的是,我可以用这一把火为后人留下一部真实可信,形象性的历史教材呀!那才是用几十万人民币所无法买来的,金铨,你说这样做对吗?”
“你翰祥兄果真是个大手笔!”胡金铨来到“远瀛观”前面,从这里可以望得见远方“观水法”建筑上正在往房梁上泼洒汽油的工人身影。越来越昏暗的夜幕下,灯火簇簇,人影憧憧。充满大战前的紧张氛围。在胡金铨看来,此地并不是在拍一场电影的镜头,而俨然是一场生生死死的厮杀决斗就逼在眉睫。李翰祥则是这场决斗的主宰和总指挥,只要他轻轻的发一句话,现代人经过几个月日夜苦干、精心施工、巧夺天工的仿古建筑,顷刻间便可以化成灰烬。如果李翰祥情愿他所拍的影片《火烧圆明园》在关键的场景上失真与虚假的话,那么他可以为京郊的大地上留下一座新的人文景观,也可以让更多的旅游者在这里观赏“大水法”和“远瀛观”等建筑中想起大导演李翰祥来。可是,令胡金铨从内心中深深感动的是,李翰祥似乎根本没有想到在京郊留下这座占地一万余平方米的仿古建筑,对他来说会有什么好处。李翰祥所想到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来追求未来影片的历史真实感!胡金铨虽然多次获得过国际上的电影大奖,虽然他所拍摄的电影畅销东南亚,名气日隆,简直可以与他的兄长良师李翰祥媲美或并驾齐驱。可是,在李翰祥行将下令纵火焚烧这偌大一片可以乱真的艺术建筑珍品的时候,胡金铨也暗忖他自愧不如!胡金铨说:“翰祥兄,你回内地拍片这条路走对了,这与当年你拉人马去台湾搞‘国联’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了!祖国各界能够为你提供这么良好的拍片条件,这是在任何其他地方也办不成的!……”
灯光闪烁着,映红了李翰祥兴奋激动的脸膛。他感到胡金铨的话是说到了他的心坎上。李翰祥深沉地颔首说:“金铨你说得对。我想回祖国内地来拍片的愿望,早已非一日了!我们是炎黄子孙,在我李翰祥仅存的时间里,我很想为十亿人民拍几部好影片的!虽然这些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很愿意这样做!……”
胡金铨遥望着远方耸立在漆黑天幕下的燕山余脉,那博大而辽阔的山峦田畴在夜色中无边无垠。相形之下,眼前的“大水法”等建筑又顿时显得十分渺小。他忽然从衣袋里拿出一张香港近日的《××日报》来,对李翰祥说:*翰祥兄,你知道吴思远这个人吗?也就是在邵氏公司当过场记的那个上海人……”
“当然知道他。”李翰祥有些诧然,猜不到胡金铨何故在他即将开始拍摄“火烧”大场面的时候,突如其来地向他提起一个与他毫不相关的邵氏公司导演来。李翰祥说:“吴思远是我在台湾办‘国联’的时候进邵氏公司的。我回到邵氏以后,记得他在《龙虎斗》一片中当副导。1971年他就能独立导片了,记得他先导《疯狂杀手》,后来又导演过《廉政风暴》,当时在香港是很有影响的年轻导演。我记得他在1975年后拉出去,自己搞了一家思